在他北京宽敞的工作室里,四周摆放着刚刚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的满誉而归的画作。王衍成深吸了一口气,仿佛那颜料馥郁的芬芳一下把他带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我最早一次拿起画笔是十四岁的时候,那时候,家里面怕我学坏,让我拉了七年小提琴,还有二胡,我拉的挺好,还当过乐队指挥。我的一个邻居是给电影院画海报的,我总找他玩,也临摹他。母亲起初不希望我学画,还把我的画箱子砸过两次。70年代画画没有出路,出来就是在文化站写写大字报。家里希望我做医生,在大学里当老师,但是没办法我就喜欢画画。后来我的父亲就安排我进采油队当了采油工人”。但命运再次眷顾了他,中央美院的师生来到了他所在的油田体验生活。“我记得有一个叫李化吉的老师,还有冯珍是留苏的,我就开始跟他们学素描,进步还挺快。而后父亲的战友介绍我到何孔德和高虹的工作室去学习。他们两个人当时是中国最好的革命军事画家。他们对我有影响,但是当时我还不能完全吸收,因为没有更多时间。”

古田会议 何孔德 1972
“我记得当时毕加索来中国展出,我的一个老师说这根本不是画画,叮嘱我不要去学,一定要画革命历史题材,这样画作的历史价值才能越来越珍贵。我理解为什么当时他们看不懂毕加索的画,可能风格和文化差异太大。你若不在那个文化当中根本就体会不了那种松弛的味道,看到的都是形,而不是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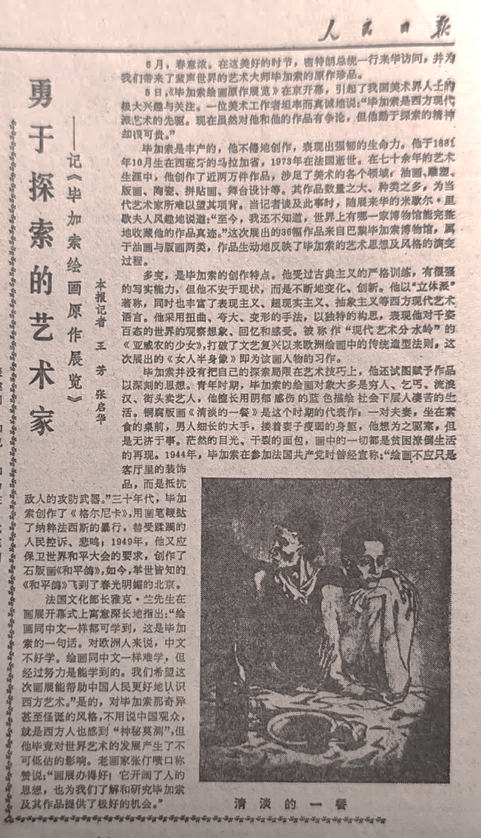
《人民日报》文化版
事实上,形神之辩一直是中国哲学艺术和宗教的一对极为重要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我国南宋著名画家、诗人,王微在《叙画》中就曾有言,绘画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傅抱石1998:34)。老子的《道德经》也曾论述“形”作为宇宙创造的显现部分,以及它和“神”这个未显现的存在的关系。“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形与神无时不在转换舞蹈,每当人去捕捉形,神却狡猾地逃脱了,真可谓“道隐无名”。有趣的是,王衍成对于那未显现的“神”的探究之路却起源于在法国圣艾蒂安大学艺术学院求学的时候的经历。
“我刚到法国学习的那段时间既不服气他们的那些画,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画,痛苦了很长时间。我花了十多年去体悟这种自由,我在法国这么多年,对我的教育和生命状态自由的释放特别重要。它的文化土壤和松弛的状态是独一无二的。我变得可以在自由的状态之下去发现一种生命体,并与之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持续不断地探索着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身份。
“在我与阿奎维拉及其他画廊合作十多年的过程中,周围的确都是历史一线艺术家的作品,例如马蒂斯,毕加索,培根。你很容易被美术史压倒,你会被他们绘画的语言压倒。大概十年之后我有了一个顿悟,其实他们每一个人是找到了去显现他这种语言的明确性和纯粹性的一种维度,这就是他们离艺术创造原理更近的那种通道。”
“如果马蒂斯和毕加索接纳了你,他是接纳你的灵魂,接纳你这个生命个体,说明你这个晚辈可以唤醒他们生命的一种原创力,他不希望你照抄他们的某一种色彩或技术,面对所有艺术史你是抄不完的。每个人生而为人都带来了你独特的DNA,在美术史中洗礼之后需要再将它放下,慢慢产生你的一种状态去画画。这时你的笔没有哪一笔应该怎么下,不应该怎么下,你的所有不经意,所有事故,都是一种偶发的美的存在。如果你静下来思考再去画就又是在已经成形的体系中游走了。最美的东西都是在半事故的状态下,就好像要失败了的那种状态下产生的,不是吗?”

无题 王衍成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