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何为?什么是书法理论?何为书史?书法史是艺术史还是文献史?对于当代书学而言,以上问题并不是自明的。抑或说,在当代书法理论尚缺乏学科反思的背景下,以上问题尚无法得到学理化的阐释和揭橥。书法作为一门后发学科,在20世纪相较于文学、哲学、历史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落后半个多世纪的情势下,无疑又加剧了对上述问题认识、接受和阐释的复杂性及现实困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至迟到20世纪30年代,在现代人文学科领域,无论是文学、哲学、历史学、美术学乃至文艺学都获得了学科化推进,而书法却由于被摒拒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之外,而不断被边缘化,以致由倡导汉字拉丁拼音化,谋求取代汉字,书法也随之处于命悬一线的文化孑遗状态。这表明书法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中被抛弃的命运。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整体而言,书法始终处于非合法性的危机境地,根本谈不上学科化和理论化建构。在这期间,除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对书法美学作了有限的启蒙外,书法理论始终处于边缘化的落寞境地。
书法的现代性(modernity)启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学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全面融合、碰撞而发端的。书法由此走出认识论困境,而谋求本体论转向。这一转向是由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价值重估与西学的方法论推动这两股思潮的合力而实现的对传统文化包括书法进行现代性阐释乃至本体论的确立。书法从而获得了现代性境遇的美学观照。随着书法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书法理论家通过中西视阈在本土重新发现书法历史,并为书法加以艺术哲学理论而“命名”:书法是抽象的艺术符号。这为书法理论开启了现代审美源流,并推动了书法理论的价值重建。
客观地说,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和哲学方法论的全面涌入,引动了文化热、美学热、方法论热。在这一背景下,书法理论以及书法学科建构迅猛跟进,与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学科保持同步,并在艺术史与学科理论自觉方面保持着警醒状态。这一时期,陈振濂主编的《书法学》、邱振中的《书法的形态与阐释》,在书法学科与书法理论谱系建构方面,达到了当代书法理论的历史高度。从这个角度言之,当代书法学科和书法理论前设建构在20世纪90年代已获得历史基点。然而,由于知识界分化和保守主义的学术转向,书法界以文献考据为主导而形成的书法史研究权力话语,严重抑制了书法理论及艺术史与艺术美学的学术进路。这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书法理论及艺术史研究的极端弱化与中断。在书学界,书史考据文献研究取代了书法理论、书法美学以及书法艺术史研究;混淆了文献考据与书法史、书法史学的区别,划界不清,导致学科误置;时至当下的很长一段时期,理论批评、艺术史、书法美学研究被普遍忽视,在书法硕、博士教育培养中,书史文献考据成为单一普遍的学位论文写作定向。在近二十余年的书法博士论文中,书法理论(包括艺术史、美学研究方向的论文)较之文献考据研究所占比例极少。近年,书法与美术并列为一级学科,但长期以来对书法理论批评以及艺术美学的忽视,从根本上制约并影响着书法一级学科建构。因为书法一级学科建构的主体——书法史(主要是指书法史的理论阐释)、书法理论(相当于书法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揭橥)、书法批评(指书法批评理论模式、方法)皆为理论形态,因而,缺乏理论谱系的陈述与建构,书法一级学科就很难真正建立起来。
何谓书法理论?书法理论关涉到书法总体性问题。“理论是一种观念体系,是思想的系统组织。理论又是用来解释世界的,属于解释的体系。……理论,包含着怀疑、打量、思索、推测等意味。……理论也是一个历史性、地方性的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乃至不同学科背景中的理论意涵是并不相同的。”〔1〕它是对本土传统书论的现代阐释与重建。因而,它所面对的问题,首先应是本土传统书论的现代转换与价值阐释问题。但作为现代书法理论谱系建构,其宏观性、逻辑理性、思辨性又是来自西方现代艺术哲学支撑。因而,现代中国书法理论的体系、范畴、观念,一方面需进入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和传统书论的核心;另一方面也需进入现代艺术审美的形上层次——体现出现代艺术认识论、本体论特征。
对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建构如何可能?”这一理论价值预设而言,它无疑是立足于对当代中国书法理论现状的反思。而反思即意味着存在问题与危机。事实正是如此,当下书法理论面临的最大危机与挑战,即来自学科异化与理论批评失语的边缘化问题。
书法理论失语的主要表现在于,当下的理论批评失于话语应对策略和理论反思。例如,书法的现代性问题;书法美学的正当性问题;书法史、史学理论以及史观问题;书法史是艺术史还是文献考据史的问题;非自觉的民间书法与文人书法问题;汉字疆界与书法本体论问题;碑学小传统与帖学大传统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当代书法理论都失于应对和批评反思,而表现出失语状态。再从本土传统书论与美学的角度梳理分析,作为当代书法理论重要一脉的书法美学,却明显缺乏来自本土传统书法美学的范畴与观念支撑,而流于一般西方现代形式论,如空间、时间、轴心变化等。对本土书法美学的核心范畴,如韵、逸、神、气、意象、意境、禅境,缺乏形上本体论的审美认识和揭橥,从而使当代书法美学远离本土书法美学的深层创构。“美学在考察原始经验时,把思想——也许还有意识——带回到它们的起源上去。这一点正是美学对哲学的主要贡献。”〔2〕宗白华认为:“中国哲学就是‘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3〕
从另一方面言之,当代书法理论包括书法美学,对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及理论批评谱系缺乏广泛深入的研悟,更没有深入探究阐释西方自康德、黑格尔到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伽达默尔等人文哲学的核心。当代书法美学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学科性来,这是因为它既没有立足本土美学建立起书法美学本体论、心性论;同时,也没有深入20世纪西方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接受美学、哲学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论、图像学、谱系学、知识考古学、解构主义等,以建立起具有本土性的现代书法美学范畴、谱系和学科框架。这便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到当代书法美学和书法理论的现代性向度和能指。由于当代书法理论缺乏艺术美学的学科支撑,理论批评趋于弱化和边缘,远离历史意识、问题意识和现实原则,难以形成有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理论批评话语。同时,也难以进入观念史、思想史、审美史等现代性境遇,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批评理论、詹姆逊的文化批评、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福柯的权力话语、利奥塔的后现代批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现代批评理论,都没有有效地进入中国当代书法理论批评体系建构之中,产生有效的批评与观念张力。因而,当代书法理论批评处于延宕迟滞状态,既无力对当代书法创作进行批评介入,也无力建立起自洽的当代书法理论批评体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失语症”。
简单说来,书法理论的“失语症”与话语重建是有联系的两个方面。“失语症”源于对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失落。因此,在“失语症”下进行话语重建的前提是要深入中西文化内部,在对中西方文化深入认识理解的前提下,建构新的人文学科体系,而不是盲目激进地重写与颠覆。否则,不仅不能走出“失语症”,走向话语重建,反而会与历史真相背道而驰,离真正的学术理论建构愈来愈远。
对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和哲学美学的疏离和拒斥,造成当代书法理论批评与书法史研究的双重危机。一方面,它无力于以思想观念的阐释和批判力量介入当代书法创作与理论批评问题,从而导致“失语症”;另一方面,它也导致在书法史研究中缺乏史学理论、史观和思想史、理念史、审美史的支撑,而以实证的名义,将史料考据视作书法史的全部。所谓“史学即史料学”成为当代书法史研究的座右铭。这是由书法史作为学科研究的后发性所导致的学科误读。而对西方现代人文学科包括新史学理论的盲视和排拒,无疑加剧了这一误读与误置,以致从当代人文学科立场审视,当代书法史研究除了沿袭乾嘉史料考据一路之外,已很难真正构成书法史学形态。
随着20世纪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轴心期理论”,西方现代历史学已完成由实证主义史学向文化形态史学的转变,并与哲学解释学有机结合,使历史学由“事件史”转向对历史意义和文化境遇的阐释和揭橥。历史既不是纯粹主观的,也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期待视野下的“效果历史”。“因而历史的解释学理解之偶然性便使得这种理解不同于科学挪用性:历史理解必须不断地向自己的活动和假设提出质疑。”〔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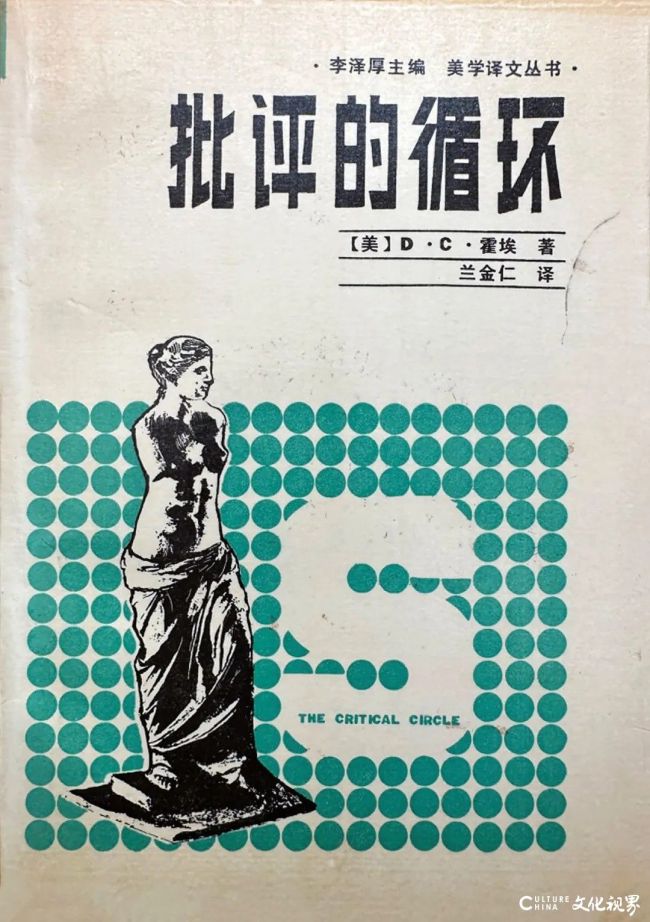
图1[美]D.C.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历史从来不会返回到同一点上”〔5〕,历史的张力和真实来自生存本体的生成与衰颓消长的文本间性。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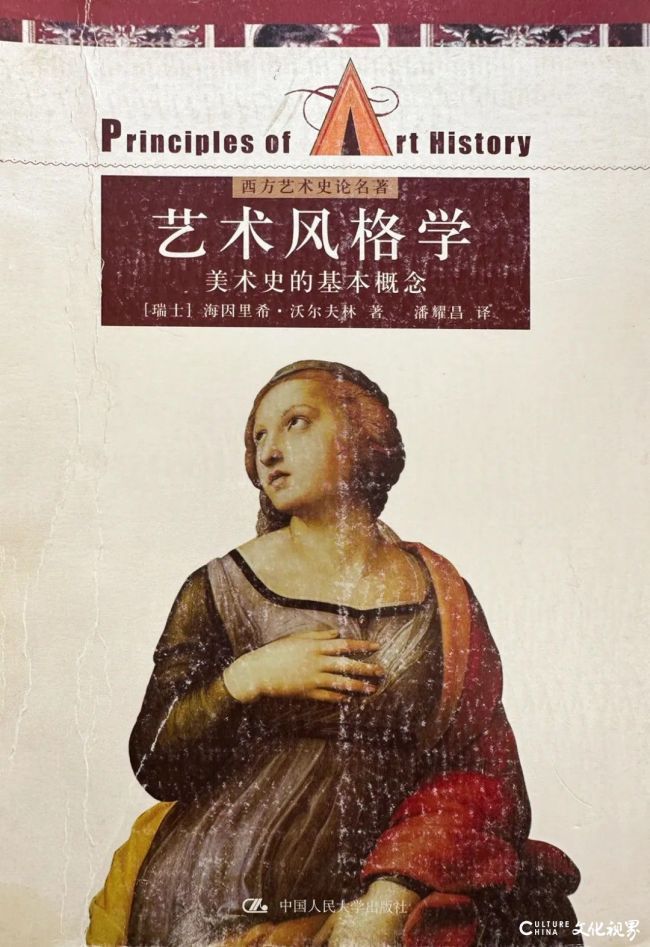
图2[瑞]海因里希·沃尔夫林著,潘耀昌译《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当代书法史研究的典范法则和方式即是求真意志下的史料考据,将书法史研究单一窄化为史料考据真伪之辨,而抽空了书法史的思想史、文化史、审美史内涵与学科间的有机联系,也就谈不上书法史的史学理论与史观内涵了。长期以来,当代书法史研究对于这种史料考据模式坚信不疑,认为这是书法史研究的正途和不二法门。细加追究,这种书史研究风气既来自保守主义的学科自大,也与书法史作为后发学科的先天发育不全和学科误置有关。同时,也与当代书史研究领域从根本上缺乏西方现代艺术哲学和艺术史理论的学科反思有关。因此,进入21世纪,当代书学谋求新的书法理论和书法史学科建构背景下,对书法史的学科反思势在必行。首先就书法史研究本身而言,书法史料考据与书法史学者之间需加以划界区分。史料考据不等于史学。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书法史研究。“史料学派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们的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主要由于他们对于史学上所谓‘客观性’的问题的了解有其局限性,他们假定历史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客观的,可以通过科学的考证而还原到‘本来面目’。如果一切事实都考证清楚了,那么全部的历史真相自然会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乐观地等待着‘最后的历史’ (ultimate history)的出现。正是根据这一假定,史料学派才否认史学和时代之间有任何关联。这一学派的人深信,纯粹客观的史实既能通过一定的考证程序而恢复其‘本来面目’,则史学家因自身所处的时代而产生的一切主观因素都已被摒除在史学之外了。”〔7〕在历史学界,史学、考古、文献考据三分天下。考古学家与文献学家的工作目标与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一是以田野考古的地层出土文物勘探;一是以文献史料的真伪梳厘考辨,来为历史学家提供实物文献的可靠史学研究基础,虽然它们是整个历史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但其本身则构不成史学研究。史学研究是历史学家对社会历史形态、特征及嬗变规律的历史文化阐释。其中蕴含着历史学家的史观模式。这种模式因历史学家的历史文化视野、价值观念、分析框架,以及所据历史文化立场不同,从而体现为不同的历史流派和主体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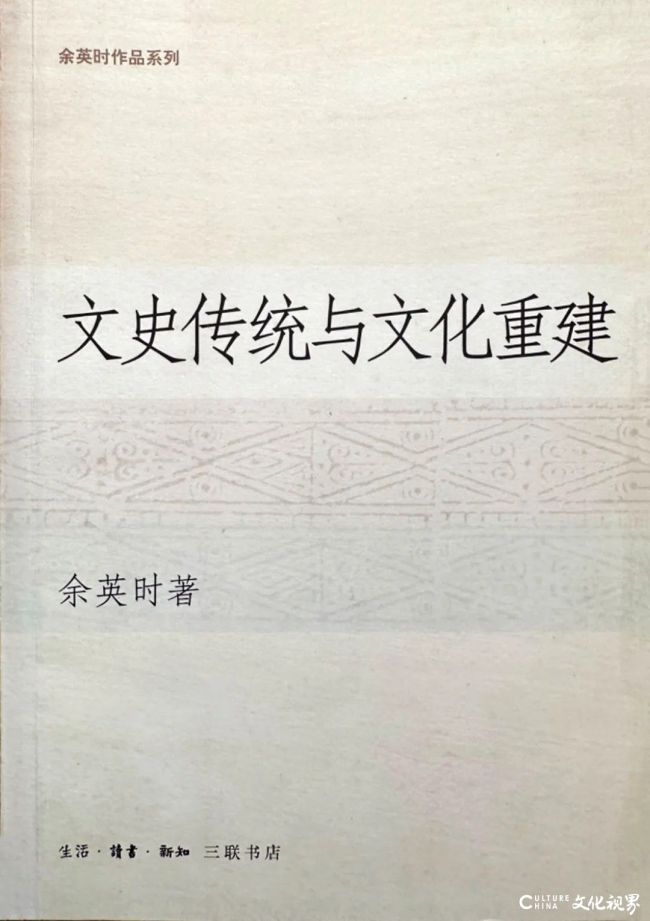
图3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因此,在现代历史学大家中,即使被推为以史料考据胜的史学人物,如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也并不完全耽于史料考据,而忽视历史意义的阐释与史观的确立。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便石破天惊地揭橥出殷周社会历史文化的巨大转捩的内在动因在于从巫史文化到礼乐文化的转变,而其内在政教伦理则是从崇天佑神到敬德保民的转换,并贯穿着德、礼对天的超越。这成为殷周社会历史研究的经典论述,也是对殷周社会历史发展的史观揭橥。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写道:“《表记》上所说的‘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是道破了这个实际的。……这种‘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几篇文章中就象同一个母题的和奏曲一样,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的确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则以种族、文化、门第三要素阐释隋唐社会历史制度嬗变的内在关联,并揭橥出关陇文化和均田制这种源于北周北魏的文化政治制度对隋唐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开创了隋唐历史研究的新局。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疑古派”史观,打破了上古三皇五帝神话传说与真史杂糅不分的混沌状态,还原并揭橥历史真相,指出“愈到后来传说中的古史愈长”的“层累地造成”的主体史观。可以看出,真正的史学必以史观为基础。没有史观的史料考据构不成真正的史学。因此,史学一方面牵系着历史的意义,一方面联系着历史的阐释。这便自然牵引出史学理论。当代书法史研究所存在的困境,即在于缺乏史观与史学理论支撑。在史料考据中,失去历史意义追寻和历史阐释的价值。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认为:“精神冲突作为两种精神传统的相遇,也是一种开启精神的未来向度的意义显现过程。倘若精神冲突被化解为实证考据式的对比,成了寻找模式、结构的异同,无异于当今的中国精神把自己排除于历史的未来向度之外,与历史文本的意义显现以及现时历史中的意义建构根本无涉。”〔9〕更进一步言之,书法史本属于艺术史,而不是文献考据史;因为艺术史与一般史自有着本质的不同。艺术史以审美立场融合美学史、观念史、文化史、趣味史,揭橥风格的视觉含义与母题,因而风格成为艺术史的主导动机。“风格是艺术史的基本概念,这是因为艺术史的基本问题只能根据这个概念才能被系统说明。”豪塞尔在《艺术史的哲学》中写道:“历史的诸结构,例如传统、习俗、技术水平、流行的艺术效应、盛行的趣味原则、主要的论题等等,确立了客观的、理性的、超个人的目标,对心理功能的非理性的自发性确立了界限,并与后者一起形成了我们称之为风格的东西。”〔10〕
由此而言,当代书法史研究将艺术史一味拉向书法史料考据,难以揭橥风格的含义和主导动机,以及美学与文化史、思想史融合的有机境遇,是典型的学科误置。这从而使书法史研究与艺术哲学和理论批评失去了内在联系,以实证主义歪曲了艺术史的人文学科性质。从当代人文学科的发展而言,无论是艺术学、哲学、史学,还是美学,都经历了世纪性的观念转换。例如,哲学由理性哲学转向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消除了逻各斯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价值观,由理性本体走向生存论本体;历史学则由实证主义转向文化史学。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夏商周、春秋战国和秦代社会性质讨论,早已因观念陈旧而被弃置。在美学领域,有关美学性质的讨论也被美的生成论取代,认为美不是绝对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美的本质。美是随着人文精神和审美境遇的嬗变而不断生成改变的。“美不只是一个艺术欣赏或艺术创作的问题,而是‘自然的人化’的这样一个根本哲学—历史学问题。”〔11〕因此,当代书法理论包括书法美学应追随当代人文学术发展,保持学科理论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围绕现代性这个主轴,建立起既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又超越于内在本土文化传统,而与西方现代性构成自洽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注释:
〔1〕邢建昌《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反思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2〕[法]米盖尔·杜夫海纳著,孙非译《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3〕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4〕[美]D.C.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5〕[瑞士]海因里希·沃尔夫林著,潘耀昌译《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9页。
〔6〕[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24页。
〔7〕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64页。
〔8〕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9〕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10〕[美]阿诺德·豪塞尔著,陈超南、刘天华译《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205页。
〔11〕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7页。
(来源:美术观察)
书法家简介

姜寿田,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河北美术学院教授,河南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获第三届青年理论家书谱奖、全国隶书学术研讨会二等奖、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提名奖、第三届中国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曾出任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评委、第八届全国书学研讨会评委、第二届全国草书论坛评委。
出版专著:《中国书法理论史》《中国书法史绎·本体卷》《当代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史》《现代书法家批评》《现代画家批评》《学术与思想·书学论稿》,主编《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书法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