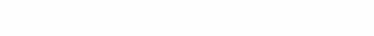真正的喧嚣在背景里。那是另一座塔,用图像碎片砌成。画家把眼见过的、牢记着的世界,都糊了上去。马蒂斯的人体,勃纳尔的浴女,马特伊科的小丑,利希滕斯坦的恋人,一张拥吻的照片,列宾、高尔基、托尔斯泰站在泥路上……霍克尼的《艺术家肖像》在女孩右臂旁,一个人站着,俯视泳池里的另一个人,隔着甜蜜的疏离。霍珀在另一边,一个裸女坐在窗边,望着外面,那是后资本主义的孤独。还有唱片,大学时代最喜欢的乐队。Metallica同名专辑封面上,那条蛇盘踞着,冰冷。画的时候能听见《Nothing Else Matters》的贝斯前奏。交流注定失败,喧嚣终归空虚,“Nothing Else Matters”成了庇护,一种主动的聋。画家把蛇画上去,把那种轰鸣的寂静画上去。下边是少年时代通宵读完的《罪与罚》,挨着切·格瓦拉……还有卡茨与Nirvana。
画家把它们全部并置,挤压,重叠。当这些图像被强行塞进同一个平面,故事就消解了。它们不再说话,变成了一片颜色与形态的噪音。这是画家的巴别塔。不是勃鲁盖尔那座石头建筑,是座用碎片、回响、情绪堆砌的塔,永不完工,内部轰鸣。画家是建造者,也是塔中的人。
画面里有两座塔。一座是书堆的,脆弱,但有秩序。另一座是记忆的碎片,放射着、构成一片喧嚣的背景。女孩站在中间。她不看塔,也不看背景。她微微低头,手按着帽檐,像在抵御,又像在倾听。她是喧嚣中的标点。

巴别塔抉微-2
画画是复杂的手工。画家不想画面只是叙述,也不想它沦为抽象。画家想让“喧嚣”能被触摸,让“寂静”具有形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这片背景就是画家嘈杂的“家”。梅洛-庞蒂说,我们通过身体在世。那个女孩的姿态,就是一种身体性的在世——一种沉默驻扎。
有人喜欢这幅画,说看到了坦诚。有人不喜欢,说闻到了矫饰。也许都对。画完成了,它就独立了。它成了一个物体,面对所有可能的注视。
在展厅里,画家想,如果涂掉这女孩,在左边也用书,堆起另一座塔,略低点,两座塔的画面会怎样?但这只是个念头。绘画有无数种可能。每一张完成的画,都是一个句号,可能成为下一个问号的开端。
画家解释自己的画是可笑的,不过,可笑也是一种解释。很多事情,想做,没做成。很多事情,未必想做,却成了。意图在落笔时就开始偏离,画面有自己的意志。它最终长成的样子,常在预料之外。这就是创作。
画家把画命名为巴别塔。不只是因为那个圣经故事,而是因为,画家感到我们每个人都在用毕生收集的碎片建造着什么,固执地,可能也会是,徒劳地。这么解释不知道是否高级。
但,画家画的,就是这个。
(文/邬大勇)

巴别塔抉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