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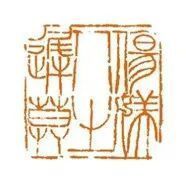
释文:伤美人之迟暮(清黄牧甫)
受乾嘉学风所影响,在文人士大夫的圈子形成了好古尚古以及刻求古意的鉴赏文化风气。邓石如在这个语境下,将汉隶和汉印的风格面貌转述到秦篆,以小篆的手法,在更强烈的“古意”意识驱动下,发出了自己激情澎湃的声音。就像东晋王羲之一变古法而为流畅之美的新体那般,邓世如是历史上第一位将书法与篆刻,笔法与刀法和合为一的印人。他将书法笔墨之美融入于篆刻,创造出以流美而不失磅礴气势的“印从书出”美感类型。另外,此前的篆刻主流充满了文人的理性色彩,其后多元的甚至于是非理性的元素与之分庭抗礼。于是,篆刻在他那里发生了转向,成为中国篆刻史上第一位开宗立派人物,开创了中国篆刻的新纪元。
由文彭、何震、丁敬、邓石如形成的一个篆刻的经验事实链,到了赵之谦那里形成了文采风流的经验事态。一是赵之谦对碑学一种扬眉吐气般的深入,作为清代最有力的碑学理论的实践者,他的篆隶楷行草都是碑派技法,并形成了趋向完善的技术体系,以北碑新体的面貌横扫帖学媚弱的书风,作为真正的碑学典范而影响至今;二是他的刀下古玺、汉印、宋元朱文、诏版、权量、汉镜文、钱币文、瓦当文、封泥等信手拈来,一并入印,多元的美感并呈。在边款的开拓上,赵氏参照汉秦砖汉瓦图形,北魏造像样式,人物造像,长文题跋无所不用其极;三是作为“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他的写意花卉以书、印化入,开创了有浓郁金石意味且色彩斑斓的海派画风;四是在学术考据上他著《国朝汉学师承续记》、《补环宇碑访录》、《勇庐闲话》、《辑雅堂诗话》等。赵之谦以“印外求印”实践观,取法宏阔,前无古人,勇猛精进,创造性地开辟了富于“移情震荡的发抒之美”新境界。几个“事态”可以构成一个复合事实,赵之谦的艺术多元合并纷繁的事态,复合一切事实地构成整个篆刻史的经验世界,成为中国艺术史上首位集诗、书、画、印、文于一体的集大成者。其后,浙人吴昌硕以朴茂峭刻的精神境界,创造了苍郁沉雄的风格。黄牧甫倡导三代以上的“吉金美”,所作印面绝去剥蚀斑驳古态,开创出篆刻光洁整饬,妍美典雅的新境界。其后,“化构期”篆刻的创作局面的开拓大多在用刀的意味上去考究。比如齐白石单刀冲切为主,辅之复刻的一种运作,将刀的锐利感表现得十分充分;又以字法笔划的空间措置,经营出一种强悍而不失婉约美的印风。
如今艺术创作发展在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支撑下,篆刻艺术在中国传统美学的“比德”、“缘情”和“畅神”三大审美范式之外,更加趋于“写实”。在社会分工更加细密的今天,受当代科学主义影响,人们的审美更加多元,趣味更加以“物”的真实性去选择自己的爱好与追求。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篆刻也不可避免地趋于大众审美需要,在形式上对篆刻提出了多维的设计性要求,讲究精密的设计和完善,讲究风格化,形成类型或样式的批量产出。
以上关于中国印史四大分期的宏观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一时期十分漫长,但从“篆刻”的角度来冷静明晰地看待和理解中国印的整体历史,会发现作为篆刻的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长。如果考究一下我们目前用于篆刻的智力游戏,考虑到我们正在为篆刻的当下做些什么的时候,这些探讨可能会触碰和启始我们重新思考、发现和认识中国印史之“元智力”,在这个瞬时的空间里会接收到超越刚才你正在想和做的事情之新指令。如此看来,篆刻所做的事情方兴未艾,篆刻史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历史,才能运用我们更明智的判断力去把握当代中国篆刻的发展方向。
五、当代中国篆刻审美体系的架构
改革开放以来,书法篆刻从业者长期处于东西方艺术形式与观念的纠缠共生语境中,在认知上他们较古人已有疏离传统的倾向,实践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各种艺术样式的创新,诸如新观念、新风格、新趣味、新媒材等等,一旦诉诸书法篆刻并对之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创新尝试就会显得无所适从。对于篆刻固有属性中的客观要素,我们大家是有共识的,而对于篆刻固有属性中的主观要素,如审美意蕴、艺术观念及其发展方向,大家可以达成共识,也可以莫衷一是。鉴于这一状况,架构当代中国篆刻的价值判断体系,确立当代篆刻艺术创作应有的美学品质,势在必行。我们选择历代诗论中最能集中揭示中国古代艺术内涵、最能体现中国品评形式的诗论,即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二十四种审美品格,以意象和意境对各种品格做出隐喻和通感式描述,虽用语言却有着不落言荃的“心印”特点。在此基础上,笔者以印品艺,结合当代篆刻艺术实践的“样式实在”,将此二十四种审美品格进一步概括为四种审美类型,以划分古今篆刻追求的美学范畴,展现其中所蕴含的当代人文精神。
隐喻原型的古雅之美:这里的“隐喻原型”是指与经典的秦汉古玺印(包括但不限于此)在形态上较为接近、在神采上息息相通。因为作品充分保留了古代经典印章的风格神韵,所以这一类的篆刻作品虽未强调面貌上的独创性,但却体现了精深的传统功夫和古雅深沉的历史情愫。正是在此充满历史情愫的回顾中,美感才从作品的怀古幽情之中显现出来。这种审美类型不仅适用于那些“印中求印”的艺术风格,在很多强调“印从书出”的流派印风中也可得到充分体现。该类型与司空图所谓的“高古”、“典雅”、“含蓄”、“雄浑”、“劲健”等审美品格可以互通。
错金镂彩的雕琢之美:这一美感类型对应于古代文论中的“错金镂彩”之趣味,是指篆刻中运用细腻的刀法去传达精整的篆法与微妙的笔法,或者单纯着意于极为精工的装饰性线条,从而呈现出一种充满精致之“静”的工艺之美。这一类型虽与“清水芙蓉”的传统文人趣味有所偏离,但在大众化审美潮流的当下,其存在与发展有着充分的理由。实际上,近代篆刻中精工的元朱文与鸟虫篆等样式,就是这一类型的充分体现。该类型中的“雕琢”表述强调了工艺的高度“精美”化,与司空图所谓的“绮丽”、“缜密”、“清奇”等品格可以互通。
移情震荡的发抒之美:该类型追求野逸的天趣,具有最充分的表现倾向。它是庄禅哲学在篆刻艺术美感中的体现。“移情震荡”的审美意象象征了高蹈独立的精神品格。特别在“印外求印”的创作理路中,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玉器、岩画等纹样,乃至具有独特地理地貌的自然山水形象等等,都在这种审美类型中转化为内心的情绪体验,进而通过特定的篆刻语言得到隐喻式的传达和表现。所谓“发抒”,对于创作者而言,也就是利用篆刻语言进行精神表现;对于鉴赏者而言,则是透过篆刻语言和意象进行内模仿式的审美体验。该类型与司空图所谓的“雄浑”、“高古”、“自然”、“疏野”等品格可以互通。
奥赜寓言的抽象之美:这一类型强调特立独行的创造性,以一种精微的义蕴,含蓄而深奥的理性经验,去呈现一个抽象的趣味特征。这种美感充分体现了现代艺术理论所强调的“陌生感”,因此,不仅在字法上往往古奥难识,更重要的是印面形式语言的抽象感,须在刀法、字法、笔法与章法等方面出人意表。这种类型的美感在最初接受上常令人困惑,但却并非无源之水。一方面,古代玺印早有这种风格趣味存在,而且在“印外求印”方法的激励下,古迹遗存中诸如部分青铜器纹样、陶纹与高古岩画等都有相似表现样式。另一方面,在当今视觉文化研究日益广泛和深入的文化环境下,以保证篆刻本体语言的为前提,很多异国文明中的视觉形式要素同样可以借鉴入篆刻艺术当中。这种审美类型可与司空图所谓的“委曲”、“流动”等品格互通。
上述四类审美类型囊括了当代篆刻风格追求的大要,逾越了单纯以“古意为贵”的传统文人篆刻审美。相对于书画艺术,中国篆刻虽然成型较晚,但却是建立在象、意辩证关系这一牢固的艺术观念基础之上,在当今中西文化频繁互动以及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语境中,作为民族传统艺术门类之一的篆刻,无论在创作还是品评上,既要从传统文化中来,又充分考虑了当下视觉艺术现状,从而能够为篆刻形式语言的新发展提供动力和保证。实际上,当代中国书法理论研究与创作的审美“终端”,同样可以这四种审美类型划分。时代需要我们为当代中国书法和篆刻创作建构在一定理论意义上比较完善的“当代中国书品”、“当代中国书品”的价值判断体系。
(文/魏广君,2024年12月11日晚8:55初稿于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来源:京华印社官微)
艺术家简介

魏广君,1964年生,河南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博士。现任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所长,京华印社社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