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时,我期望每位同学都完成两项工作:第一项,创造一个专属的“立方体”(cube),里面是自己的“小世界”。当时我们尚在探索Second Life这类平台。学生如同创世神,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设定规则与美学体系。例如,构建一个纯粹的水墨世界,进入其中,万物都是水墨化的,足迹、风影皆然。或创造一个规则反转的世界,远近反转,上下易位,颠倒梦想。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颇为艰难,但今天就可以实现。通过模态与规则驱动的世界建构,多么有魅力!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小世界的创造者与经营者,使之不断生长。这便是后来我倡导的“洞天计划”的雏形:鼓励个体构建无数风格迥异的“洞天”,当这些独立世界相互连通,将交织成一个如万花筒、曼陀罗般无限丰富的多元宇宙。(图4、图5)


图4、图5洞天:国美在线艺术社区(CAACOSMOS)及其自组织的艺术活动界面图片来源/中国美术学院
“洞天计划”的目的何在?旨在以这无量大千世界,对抗我长久以来的深切忧虑。自1999年《黑客帝国》上映时,我便坚信,若人类无所作为,那电影中描绘的黑暗未来终将成为现实:肉身沦为电池,精神沉溺于虚幻,现实化为荒原。某种意义上,人类正持续地滑向这一深渊。当下,我们看到,“黑暗启蒙”、科技加速主义与公司帝国主义这三者的复合体,正在大洋彼岸滋长。其未来导向,必是某种形式的数字集权主义、技术种姓主义。我们必须以无比丰富的、多元的无量世界,去替代那个统一的、无缝隙的单一度量体系(matrix)。它所谓的“原乡”(如《黑客帝国》中的Zion),不过是被虚拟出的狭小缝隙中的桃花源,在第三部影片中,其脆弱性和虚伪性暴露无遗。
创造多元的可能世界,正是艺术家应肩负的使命。最伟大的艺术创造无异于“创世纪”(genesis)。随着科技的发展,我越发坚信艺术家有此能力,至少在符号形式(symbolic form)的意义上是如此。许多年轻艺术家常感叹条件和资源不足,我觉得今天的创造未必需要太多资源。近期来阅读刘亮程的作品,主要是《一个人的村庄》《捎话》《本巴》。这位隐居在新疆的一个僻远村落的作家,展现了一种“创世神”般的童真与寂寞。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看到一个自足的文学世界从一个人的天真与孤独中生长出来。刘亮程说,在村子里他才能关心远方、过去与未来;若在城市,或许反而会囿于切近的生活。我深以为然。(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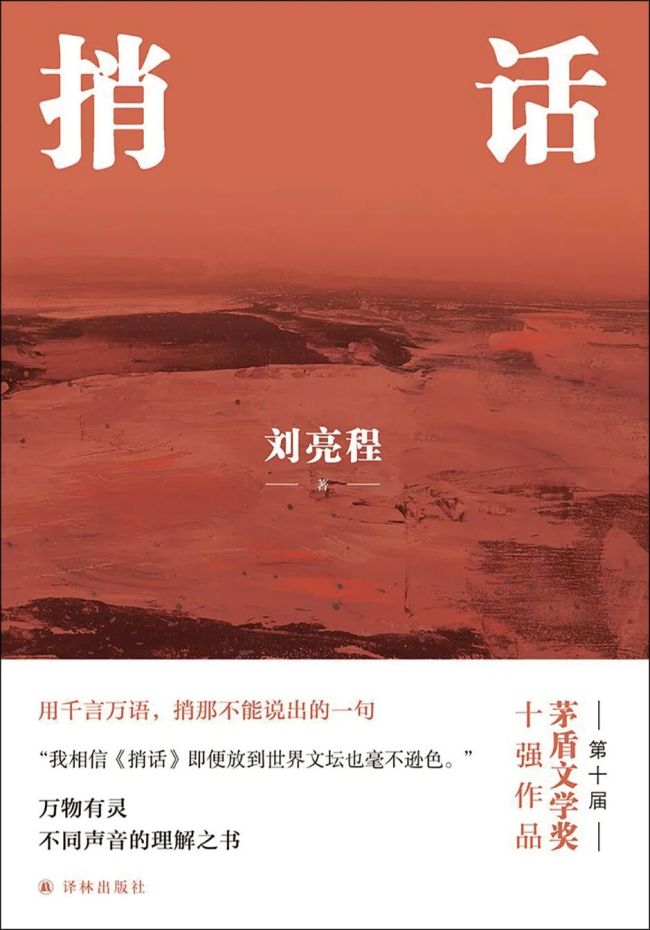
图6刘亮程《捎话》封面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