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8日清晨,我们先去了离驻地仅一河之隔的谢家沟。刚进沟,便听见流水潺潺,顺着溪流望去,几十里的沟谷里,原生胡杨林长得肆意而苍劲。我沿着溪边漫步,脚下的碎石被流水磨得光滑,身旁的胡杨姿态各异:有的树干粗壮如柱,树皮皲裂如老农劳作的手,刻满了百年风雨的痕迹;有的枝干遒劲扭曲,像书法中的篆书笔画,向天空自然伸展;还有些千年老树已经倒伏在地,却显得横亘倔强;亦有近十来年新长的小树,树干挺拔,枝叶嫩绿,透着少年人的朝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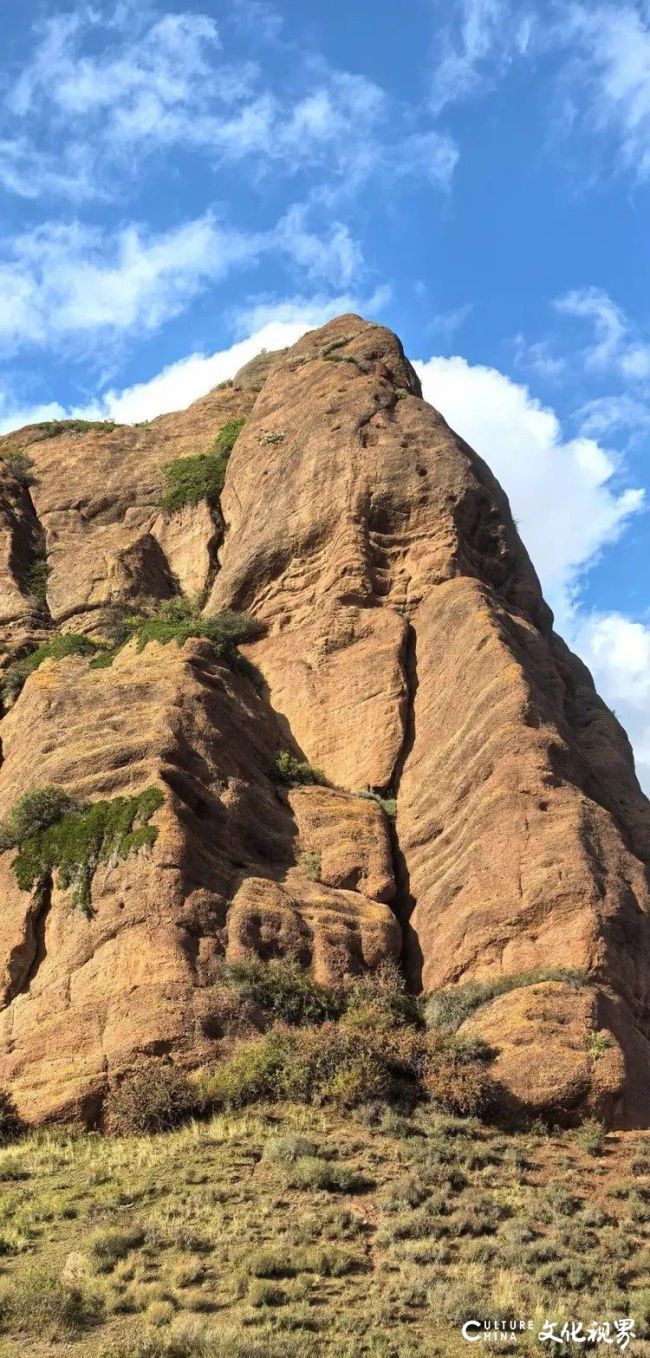
这便是人们说的“三个千年”胡杨精神——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站在林间,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来,金黄的光斑落在地上,风一吹,树叶沙沙作响。同行的画家们感慨,谢家沟是“十里画廊”,像一幅丹青长卷。这里的景,不似江南园林的精巧,却有北方山水的开阔,无论是印象派的光色,还是写实主义的细节,都能在此找到灵感。难怪有人说它是“北欧秘境”,可在我看来,它比北欧的景多了几分人文的温度——哈萨克牧民的毡房散落在林间,炊烟袅袅,牛羊低头啃草,为这幅自然画卷添了最生动的注脚。

19日去板房沟,刚出发便遇上小雨。车往山里开,海拔渐高,雨也越下越大,到目的地时差不多已是中雨。大家的衣服都被打湿,却没人抱怨——雨雾中的板房沟,藏着别样的韵致。高原草甸被雨水洗得发亮,原本的浅黄变成了中黄,像是上了一层油彩;云杉林更显幽深,墨绿的枝叶间挂着水珠。天空阴沉沉的,云层很低,像是压在山巅,太阳始终没能挑开云帘,却让整个板房沟显得格外安静。偶尔有远处传来老牛的哞叫,纯净而悠长,更衬出这里的静谧。细雨蒙蒙,我静静看着眼前的景:黛色的松针上挂着细碎晶莹的雨滴,清泉顺着山谷流淌,像一根银丝缠绕在山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