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游新闻报道,一女子发现自己的男友已婚,随后报警,她却被强制送进安徽芜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出院后检查自己并无精神疾病。4月9日,当事人胡女士对媒体表示,“我现在要追究王某诈骗罪和重婚罪,也要对强行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的相关人员追究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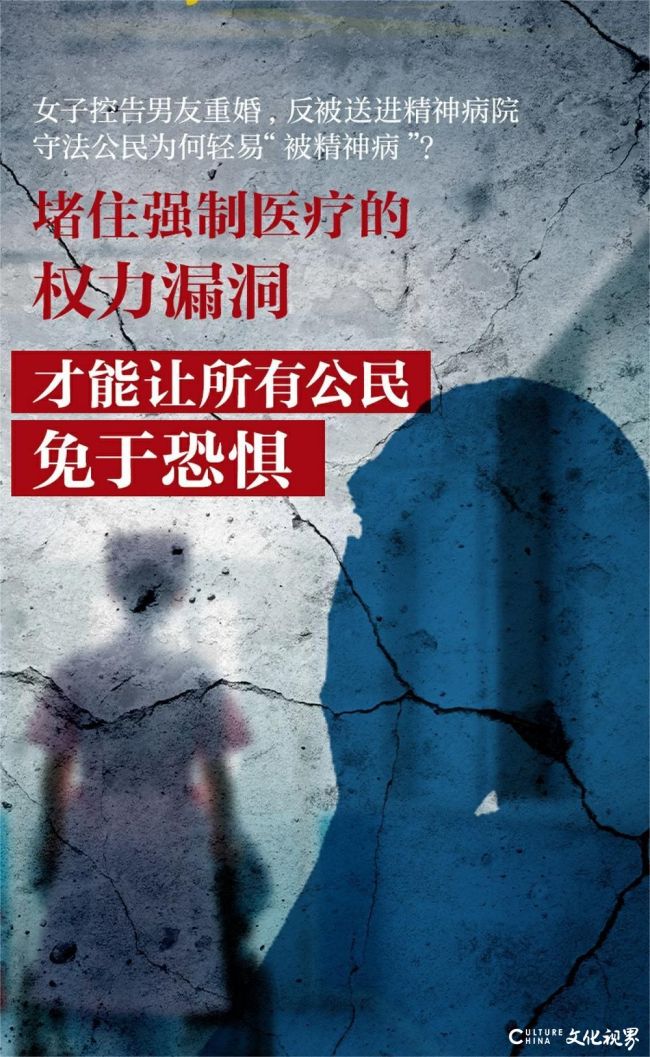
在这篇报道中,有几处细节值得关注,先是胡女士表示,“我记得到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是3月10日下午,当时听医生说,送我来的人说我是流浪人员,没有亲人,而且患有精神病。”该院医生也称,胡女士是被当地公职人员以流浪者身份送来的,其间她有多次撞门想要出去的行为,院方认为其精神有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治疗。而在报道中另一赵姓医生则捅破了上述“公职人员”说法的窗户纸,明确称系无为市一派出所工作人员将胡女士送到的精神病院。
也就是说,胡女士是由当地公安机关以流浪人员的身份强制送诊的,由此就涉及了法定程序问题。
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就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此处的法条明确了除了本人自愿到诊以外,其家人作为适格主体也可以将其送诊。法条还规定“诊断结论表明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的,由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这里提及的流浪乞讨者想必就是当地公安机关之所以要“编造”胡女士为流浪者身份的原因所在。
因为强制医疗涉及对当事人人身自由的剥夺,国际社会通行的对强制送医的“危险性标准”的认定都极为谨慎。我国精神卫生法也明确,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已经发生或有可能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时,公安机关才能越过其他适格主体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鉴于当地有关人士称胡女士有自杀倾向并有抑郁症就诊经历,此处强制送诊的必要性姑且不论。
但是,本次事件中胡女士并非流浪者,当地为何要为其虚构身份?虽然报道中医生提及期间多次联系家属,电话均无人接听。但胡女士弟弟则表示,胡女士被关在精神病院的6天里,并未接到电话,甚至是其弟弟在与生意合伙人经过多方打听才了解到了姐姐的近况,那当地为何没能联系上胡女士的亲属?因此,送诊程序的合法以及诊断结果是否准确需要当地“权威人士”的回答。
相比本次事件中当地称胡女士有自杀倾向,近期的另一起“被精神病”事件则更为离奇:安徽省淮南市市民张坡称自己在2024年6月,被当地公安机关单方面强制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检查治疗长达22天,其间被限制自由,禁止家属探望和接出院。但事发前的监控画面显示,张坡既没有伤害自己的行为也没有伤害他人的行为,且对其的强制医疗也并没有经过家属同意。
其实,在2013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施行前,关于“被精神病”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精神卫生法的施行初衷就是为了规范精神卫生服务,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在该法实施后相关情况已经好转,而近期曝光的这些“被精神病”的新闻,表明相关工作在执行层面依然有需要补足短板之处。相比只谴责某个公权部门的滥权和医疗机构的不作为,更须跳出个案,在强制医疗的整体脉络中去检查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