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中期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书法创作的革新和探索业已经历数百年,至今仍未停止。这一方面说明书体书风一直在变;另一方面也说明书法艺术创新之难。新时期以来,中国书法的探索实际遥接明清以来的书法变革之风,只不过多了西方艺术风潮的影响而已,其实质并无差别。我以为,洪厚甜是谙熟这段历史的,也清晰思考过古典与当代书法之间的关系。就洪厚甜的书法研习之路而言,始终立足于书法的脉络和源头,从没有脱离开传统而自行其是,但也并没有简单地照搬古人或者描摹前贤来获得某家某派的名头。这种鲜明的态度也决定了洪厚甜不会囿于前人的桎梏,而会力图打破固有的束缚,获得自由的书写方式。他的书法求学之路是从传统楷书拓展开来的,以他自己的说法是:“四十年来,从临写颜鲁公《多宝塔》《东方朔画赞》、褚遂良《大字阴符经》《孟法师碑》、北魏《龙门十二品》、南朝《爨龙颜碑》……一路走来,我于书法的学习研究,一直是立足于楷书的学术建设和提升来定位”。从洪厚甜的创作看,楷书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比如他的力作《苏祠重光·三苏祠灾后维修记》《杜甫千诗碑记》《新都宝光寺舍利塔修复碑记》,基本代表了他在楷书方面的追求:“浸润两汉碑刻简牍,究体势开阖之规,沉潜‘二王’一系行草经典法帖,明书圣人法交融之旨,再入唐代楷书体系,上溯北魏楷书渊薮。”在楷书的研习上,他从颜真卿和褚遂良入手来寻见唐楷之规范,再去爬梳北碑。为提高书法的“内质”,他又花了很大精力去研究篆、隶。很显然,他是希望融汇前人书法之优长,拿来为我所用,贯通为我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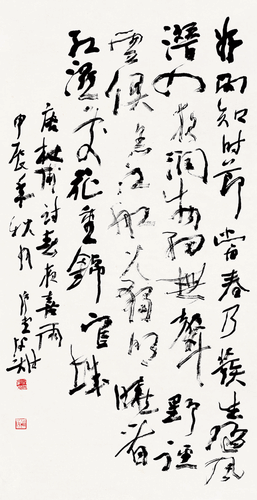
行书中堂137×70cm/洪厚甜
对于楷书的重视和反复钻研,一方面体现出洪厚甜对传统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印证了他超古典规范中寻找新的可能的雄心。正如康有为所言:“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已也。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矣。”洪厚甜将线条看做书法创作的灵魂,同时也深刻把握了篆、隶、楷之间的关系,寻找楷书形成之源头,再寻其新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在洪厚甜为数众多的楷书作品中,观者难以将其归纳为某一种既有的书体,有研究者称之为“洪体”,不过我以为这只能作权宜之计论,因为其风格形态虽已有了自己的“性情”,但仍在形成当中,其未来必然还有新的变化。如果拿2011年的《吐谷浑墓志铭》与2016年创作的《苏祠重光·三苏祠灾后维修记》和2018年创作的《杜甫千诗碑记》进行对比,即可见出,《吐谷浑墓志铭》杂糅了行书的笔法,其用笔也妍媚多姿,但后两件作品则更多地体现出碑的意味,浑朴奇丽。不过,在我看来,两者的变化并非有孰先孰后的关系,不过是洪厚甜在探索过程中的两种形态,未来如何变化还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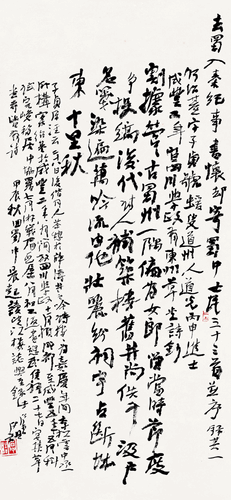
行书小品58×26cm/洪厚甜
在洪厚甜看来,碑帖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他将碑帖看做书法的一体两面,就像阴阳两极,刚的线质属于阳的一面;柔美婉转的线质属于阴的一面。碑的阳刚一面多一些,但也暗含着婉约之美;帖的东西流畅、婉转,但也内蕴着阳刚的元素。两者之间往往是相互交融、变化的。因此,在他的楷书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汉隶的古朴和魏碑的厚重,他在融会贯通中将楷、隶、碑圆熟地交融于一体,从而呈现出别样的审美趣味。早年对唐楷形态的描写到后来注重于线条的书写性,由外而内地追求楷书品质和精神。为增加楷书创作的厚重与态势,洪厚甜花费了很大精力练习北碑,再通过练习篆书去提高书写线条的质量。这样的磨练之路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00年之后。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洪厚甜的书法创作中,既能感受到流畅、飘逸之美,又可体味到苍厚、刚硬的内蕴。例如《新都宝光寺舍利塔修复碑记》(2010年),虽为楷书,但却有行书的婀娜多姿,又蕴含着魏碑的厚重感,有些笔画还有明显的隶味。另如《冯子振咏梅三首》(2021年),以草书写就,夭娇跌宕,气韵流畅,但却又能感受到浑朴之美。再如2021年个展上的《佛说金刚经》,结体拙厚,笔画骏朗,正欹相生,格调雍容简穆,庄雅严重。特别是因字大如斗,且占据一面高墙,远观更显得丰茂浑劲。从这件作品中亦可见出,洪厚甜完全打破了真、隶、魏之间的隔阂,融其于一炉,再由己出,写出活泼的生命感来,即如洪厚甜自己所言的,“写出生命,能呼吸”。

行书对联138×23cm×2/洪厚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