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穆言:“书有性情”,又说“书有老少,区别深浅,势虽异形,理则同体。”对“性情”的追求使书法创作具备了强烈的个性,从魏晋到唐,从宋到明清,书法家面目多样,且有个性鲜明。这当然不简单,不简单的原因是所谓的“性格”是养成的,而不是装扮可成的。正因为如此,书法家的养成绝非一朝一夕即可以完成,而需要长期的揣摩和探索。在洪厚甜看来,一个真正的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文化积淀、精湛的技术积累。丰富的阅历促发习书者对社会、生活、人生的感悟;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习书者提供文化的高度;精湛的技术积累是成为优秀书法家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些积淀,而且是长期的积淀,是难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书法家的,如他自己说的:“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是由优秀的土壤来产生,是需要时日的”。正由于这样的观念,洪厚甜在面对传统时始终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在技巧和学养两端加以锤炼,最终涵养出自己的书法性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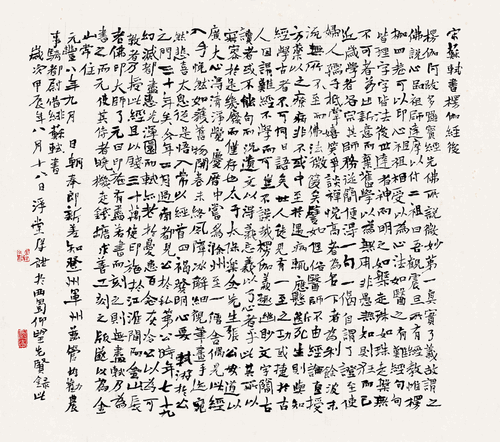
楷书斗方53×59cm/洪厚甜
所谓书家的性情体现在书体书风的个体性格上,个性意味着不同,故而它与传统法度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这其中有变处,亦有不变处。历史地看,书体风格当然在不断变化,康有为在谈及书体之变时说,“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书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笔墨当随时代,书风亦如此。但有一点也是客观事实,即基本法度不移。赵孟頫说:“书法随时变迁,用笔千古不易。”我以为这是切中要义的。但将之放置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又变得复杂了,因为在百年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否定前人是很多人心目中“创新”的代名词。现代主义绘画不就是不断否定和推翻前人向前发展的吗?这样看来,个性与传统法度之间不就存着冲突的危险吗?其实不然。对于具有两千多年积淀历史并形成一整套体系的书法艺术来说,已经形成成熟的创作体系、评价体系与理论体系。在此体系下所有的书法创作与探索都基本遵循着这一体系运行,如果脱离开这一体系去谈书法,那么不仅理论上而且技术上都是行不通的,因此以现代主义等西方艺术体系来套用书法艺术是无效的。这一点洪厚甜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认为,“中国书法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中国哲学思想最直接的表现,也就是说中国书法为什么能够有今天,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符号,就是它真正深刻表现了和传递了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和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基本的世界观。”在这样的观念下,书法的新旧关系实际就可看作古今关系。
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书法创作的古与今之变被赋予了更宽泛的意义。这也造成另一结果是,近四十年来的书法风格之多之杂已令人目不暇接,各种不顾传统基本规范的自造“风格”者也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但如前所述,书法创作还需在书法的评价体系中加以辨别分析,这并非仅以书体书风来评判新旧、古今的。正如刘熙载说的:“以篆、隶为古,以正书为今,此只是据体而言。其实书之辨,全在身分斤两,体其末也。”在固有的原则基础上寻找新的出路当然艰苦,但假使没有这样的基本法度,那么所谓的“创新”显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以为这一点也是洪厚甜清晰所见的。他在《以经典规模格局和精神》一文中,提到书法创作的高境界是“要有大的格局和精神”。在创作中,洪厚甜无论是榜书巨制,还是尺牍小楷,如《沧海行藏联》《奇逸》《佛说金刚金》《齐白石诗草斗方》等,无不在法度中寻求笔画的揖让、字势的正欹、字形的变化、章法上的活泼。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尺牍还是榜书,都彰显出气象峻厚、兴趣酣足、意态鲜明、精神飞动的艺术格局。这是具有时代气息的艺术格局。
洪厚甜的书法探索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一个极有典范价值的案例。在近四十年的书法学习创作生涯中,他苦苦追求在传统之中寻找属于当代审美精神和文化精神的道路,借古开今,拓古入今。对于他来说,书法创作既是扎根于其精神深处的源泉,也是其抒发心性的媒介。书法艺术既是回溯学术传统的路径,也是直指当代人“心象”的桥梁。明人《传习录》中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传统千古不移,无论你看还是不看,恰如当代书法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去忽略或者歪曲传统,传统依然不会消失。但如何品味传统,消化传统,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心象”,则路数各异,精彩不同了。
品读洪厚甜的书法艺术,不亦如此?
(文/陈明,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辛丑年秋月于中国国家画院,来源:《画界》2024年11月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