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展览海报上的“杜小同”是你自己题写的吗?听说你从小就很喜欢书法,书法的练习对你的水墨创作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杜:是的,海报上的字是我自己写的。我从小就对书法有种天然的喜欢,没人教。就是偶然看到字帖觉得太美了,就拿回来自己照着写。这是一种本能的吸引。
其实最初选择国画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书法。在附中时我们受的是西画训练,周围同学大多选择油画、版画,当时还有人劝我学设计,说学油画可能不好找工作。但我对那些实用性的方向兴趣不大,内心还是想追求纯粹的艺术表达。
在我看来,书法早已脱离了原有的文化土壤,就像传统绘画一样,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早已发生变化,不可能真正回到过去了。但书法本质上是一种痕迹,就像我们研究上万年前的岩画——透过笔触和结构,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唐人的书法、魏晋的风度、明代的姿态,其实都是不同时代社会关系、生产力水平和人的观念变化的反映。
所以我认为,书法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种人与世界的观念对应。如果只停留在技巧层面,写得再漂亮,也只是一个“书法的样子”,是表面的,甚至是一种“伪书法”。真正有价值的书法,是透过笔墨传递出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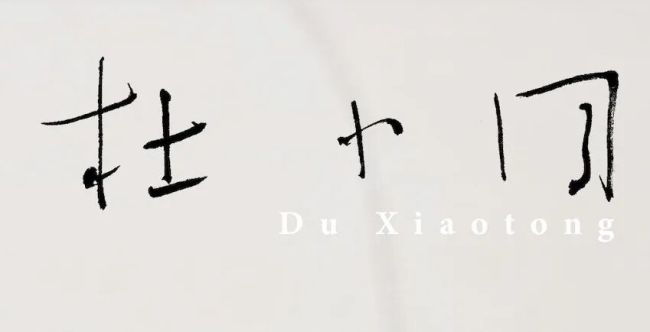
“杜小同”展览海报局部
Hi:你曾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渗透于时间的观念”,并认为“中国画自然跟时间是最紧密的,最贴合的”,能否深入阐释你对时间与水墨艺术关系的理解?这种时间观念如何体现在你的具体作品中?
杜:其实在中国画里,时空是一体的。比如我画海,不仅仅是在处理空间,更是在呈现时间的流动。我创作一张画的过程本身就有很强的时间性——比如画一根线,可能要反复画上十五六遍甚至二十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单看画一根线可能不需要多少时间,但我是非常缓慢地推进。更重要的是,我每天都会反复审视画面空间,不断揣摩和调整。这种日复一日的累积和沉淀,本身就是一种时间的体现,也会在作品中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张力。
其次,中国画本身的线条就带有时间性。无论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还是从右到左,用笔的方向和节奏都暗示着空间的延伸和时间的流动。如果你对传统艺术敏感,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书法的时序性更加明显,每一笔都有先后,不可逆转。
中国艺术,尤其是书法和古琴,时间性比西方艺术更突出。西方可能更注重空间的构建,而中国艺术则更强调时间的展开和过程的体验。这种时间性,是中国传统艺术非常核心的一个特质。

《变奏》183×145cm纸本水墨2025
Hi:你的许多画作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在视觉上,它们往往是轻盈、空灵、透气甚至是朦胧的;但观者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寂静、孤独、时间的流逝乃至生命的哲思。你是如何有意识地运用水墨的特性,通过这种视觉上的“轻”来承载和表达内涵上的“重”的?
杜:这倒不是刻意为之。如果你能看出这一点,说明你真正走进了这些作品。这正是我希望传达的——虽然每件作品未必能完全实现我的想法,但我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之所以逐渐淡化甚至去掉风景的具象元素,就是因为觉得“风景”本身会削弱我想表达的东西。它像一层遮蔽,让我真正想呈现的东西被掩盖了。这种追求其实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审美向来推崇“空灵”、“飘逸”和“远”的境界。而这些境界其实是“去伪存真”的过程所带来的感受,就像卸下慢慢堆砌的身份角色,与自我面面相觑所带来的陌生感。现实是浑浊的,需要被提炼、转化,笔墨才能干净起来,才能达到那种“飘然”的状态。
“远”,不仅仅是一种空间距离,更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的距离。人类骨子里有着对“真”和“实”的渴求,无论是哲学、科学、艺术都是对其追求的不同路径。在路途当中我们会迷醉于折射光的璀璨,但天性会让我们不满足于片段的真相,驱使我们不断的自我审视,校正,抛下熟稔,在过程中燃烧掉粗重的外壳,换得轻盈的瞬间,继续奋而触摸。

《皆是》228×558cm纸本水墨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