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的非学科性特点及其体系结构
吕东:现在我们可以转到中国美学上来了。您强调,相较于西方的学科型美学,中国美学展现出一种“非学科性”,那么您是如何理解中国美学的非学科性的?
张法教授:讲中国美学是非学科型美学,从字面上讲,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美学”,即中国古代存在着美学。中国古代对于美有十分深邃的体会,力图按照中国人自身的体会方式,从中国型的理论角度,把美以理论形态呈现出来。二是“非学科性”,即中国美学对美之理论形式的呈现,不同于西方那样的学科形态。西方的学科型美学有专门的以“美学”或“美论”或“艺术哲学”等名称形成的著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如前面所讲的,西方美学是通过把美与真、善在本质上区分开来,把专门的美感与一般之感区别开来,把艺术作为专门呈现美的领域独立出来而形成的。中国古人对美的复杂性以自身的“虚实-关联-整体”型思维去思考,有自身的独特理解。一方面,在中国古人看来,美,不可以与真、善等区分开来;美感,也不可以与一般之感区分,而是相互关联。这里“关联”二字尤为紧要。因此,中国古代美学典藉当中没有出现专门的以“美学”或“美论”这类词命名的论著,美的思想也不是仅仅在各艺术门类的论著中出现,而是出现在所有类型的著作中。相较于西方美学研究最容易在艺术门类的论著中找出美学思想的情形而言,在中国美学思想研究当中,与艺术相关的论著仅为美学资料的一小部分。中国思想的关联特性决定了中国的美学是内蕴在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的,正如中国的小说、戏曲之评点和理论是寓在小说文本、戏曲文本之中且不能与之分开的一样。如果说,山水为美,那么,正如张潮《幽梦影》所讲:“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中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丘壑深邃,画上者妙在笔墨淋漓,梦中者妙在景象变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由于中国之美是如此的一种关联性存在,因此,中国传统美学是以一种非学科的方式存在于文化的一切方面,存在于一切类型的著作之中。当然,由于艺术门类聚焦于美,由之进入中国美学是可以的,但若止步于此,就无法全面体察中国美的基本面貌。况且,中国传统艺术也与西方不同,是与非艺术的其他方面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展开为与仪式相关的礼之艺、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文之艺、与天文术数风水堪舆相连的术之艺、与士大夫庭院相连的玩之艺(其中香、茶、古物、花木、文房四宝等占有相当的地位)、与都市娱乐场所相连的伎之艺(戏曲、说书与杂耍、口技、相声等)以及与各行手艺相连的工之艺(以《天工开物》为例,珠宝、陶埏、丹青等精美工艺与舟车、冶铸、锤煅等专业工艺密切相关)。总之,中国艺术本就是关联型的。“文化六艺”展现出了中国美学的非学科性之特点。
而另一方面,中国之美,正如中国宇宙和中国事物一样,由虚实结构组成,而虚更为重要。白居易《长恨歌》写杨玉环之美,几乎不着力于外形描写,而重在突出神情气韵。读完长诗,找不到这位美人身高多少,眼形如何,三围怎样,然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却把杨玉环的美传神地呈现了出来。中国之美,在于虚实结构之“虚”。中国宇宙是气的宇宙,气化流行,衍生万物,物亡又复归于宇宙之气。中国之美就是由这气化万物而来之美,存在于气化流行的宇宙整体之中。中国的非学科型美学正是在与这样的宇宙相适应的结构中产生出来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维的整体性又决定着中国古代的非学科型美学是具有体系性的。
吕东:那么,在您看来,中国非学科性美学的体系性具体来讲是如何呈现的?
张法教授:我在《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之美:一个核心、七大方面和四种类型》,其中讲到的七大方面可以说是中国非学科型美学的体系雏形。其一,天地之性与中国之美的基本结构,主要讲中国之美以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为核心展开。其二,天地运行与中国的节庆之美,主要讲自然节气与文化节庆的合一构成了中国之美在春夏秋冬的时间运行中呈现出来的美。其三,天下观与中国的地域之美,主要讲中国之美因地域差异而呈现的多种多样的人文地理之美。其四,家国天下结构与中国的朝廷之美,主要讲以朝廷礼制为核心而展开并以等级方式呈现的人文地理合一天下之美的多样性。其五,士之家的典型之美,主要讲唐宋之后,在士人庭院中以诗、文、词、曲、琴、棋、书、画、文房、文玩、茶、香、器用、花木筑构起来的士大夫的典雅之美。其六,城市新质与中国的生活之美,主要讲宋代都城结构演变并带动全国城镇结构演变之后,由娱乐场所兴起的以大众俗情为核心的演艺之美。其七,天下一体与中国的宗教之美,主要讲道教和佛教兴起之后,在城市和山林两方面展开的宗教艺术体系之美。以上七个方面,不但突出了中国非学科型美学的体系性,还彰显了中国之美的丰富内容和独有特色。

PART.5
从世界美学史看美学研究的当下境遇及未来趋势
吕东:您上面谈到的内容已经显示出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各有特点,而且也从美学形式问题上涉及了中国、西方、印度美学三者的不同。从这里自然会引申出一系列问题。首先,中西美学,以及印度美学和其他美学,各自分别有怎样的特性,在世界美学中,各自又处在怎样的位置呢?
张法教授:这些问题大致可以从世界美学的演进史角度来予以解决。以现在的观点重审世界美学史及其演进,大体可将世界美学史分为四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时代和早期文明的前美学或曰泛美学阶段。具体而言有原始时代和早期文明之分。原始时代之美,从工具制造(西方的阿舍利斧和中国的斤斧是其代表)和仪式创造(仪式地点的建筑美化,仪式之人的身体美化,仪式器物的器形和图案美化,仪式过程的诗乐舞剧的合一)中产生出来。早期文明,以神庙为中心产生了建筑、雕塑、绘画、诗歌、音乐、舞蹈、表演的美的体系,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审美观念也在文字中有了初步的总结和体现。
第二阶段是轴心时代的理性产生,出现了三大文化中的美学,即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实体—区分—定义”型美学,以中国为中心的“虚实—关联—整体”型美学,以印度为中心的“是—变—幻—空”型美学。三大美学又分别有一系列的扩展和演进:古希腊罗马美学扩展到地中海和欧洲,形成了西方美学以及与之交迭和关联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美学,及其地理扩展而来的各类次型美学;中国美学扩展至整个东亚和北亚;印度美学扩展至整个南亚。此外还有以三大美学为核心的各文化的美学互动。
第三阶段,文艺复兴到18世纪,西方的“实体—区分—定义”型美学形成学科型美学,从而使中国和印度美学显现为非学科型美学。随着西方文化在世界现代进程中的向外扩张和全球影响,学科型美学成为世界美学的主流。同时,伴随着印度和中国以及各非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所有非西方文化的非学科型美学都开始转向西方型的学科型美学,且由于各自的文化传统,所建立起来的学科型美学又有自身的特点。世界美学第三阶段的总特点即以西方学科型美学为主的各文化的美学互动。
第四阶段,在20世纪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升级中,西方的学科型美学发生了全新的转型,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从近代美学向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最大特点是西方的“实体—区分—定义”型美学走向了与中国的“虚实-关联-整体”型美学和印度的“是—变—幻—空”型美学在根本上相契合的道路,特别体现在相对论与量子论产生的“时空合一”“质能一体”观念使西方思想从原子世界的实体性进入粒子世界的虚实合一结构,从物质的实体世界进入物质与暗物质、能量与暗能量的虚实合一结构,从以三维空间为主转而重视时间影响的时空一体作为世界和事物的新貌。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自轴心时代以来的三大美学基础所呈现的演进趋势,是中国和印度走向西方学科型美学,而西方从学科型美学向一种与中国和印度深层契合的美学升级,由此形成非常有趣的世界美学互动景观。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各非西方文化的改革浪潮带来了西方文化与各非西方文化之间新型的复杂互动。初看起来,似乎是中国和印度以及各非西方美学在走向西方的学科型美学,而西方美学在走向中国和印度的非学科型美学。但细而察之,则是以中国、西方和印度为代表的各文化美学正在科学和思想的升级中,在相对论和量子论而来的思想转变的基础上进行着一种新型的美学互动,正在朝向一种新型的世界美学的转变,重建自身。
吕东:从世界美学的四阶段来看当今的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您认为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些关于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在演进方向上更为确切的论断呢?
张法教授:目前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的演进都还在中途,因此下论断是比较困难的,但基本的面貌和特点还是可以看出一些。
先谈一下西方美学。自20世纪初的现代美学以来,一方面,西方美学在科学升级(相对论和量子论的问世)、技术进步(电文化的出现和升级)、哲学升级(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推动下也在演进和升级。同时,在由现代美学向后现代美学的演进中,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和印度美学有了哲学上的契合。另一方面,中国之道与印度之梵在促进西方思想的提升中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正是文明互鉴应有的效果。因此,西方美学要完成自身的提升,需要中西印美学在深层次上的思想互动。
再讲中国美学。中国在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后,在与西方现代美学以及学习西方而后来居上的日本美学和苏俄美学的互动中,从古代的非学科型美学走向了西方的学科型美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虽然业已建立起中国式的学科型美学,但仍在发展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西方美学译丛大量引入,西方美学思想不断地为中国学人所熟知,一种新型的中西互动在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料的大量发掘使得我们对中国古代美学的重新认识也在持续进行,一种新型的古今互动在不断加深。同时,各非西方文化的美学思想也不断传入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日本以及其他文化的美学作品都有中文译著。中国学人已经全方位地进入与世界各文化之美学的对话当中。现在,对于中国美学来讲,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对中国美学从古到今的演进进行新的总结,对世界美学的演进进行新的总结,从而在提升中国美学的同时推动世界美学的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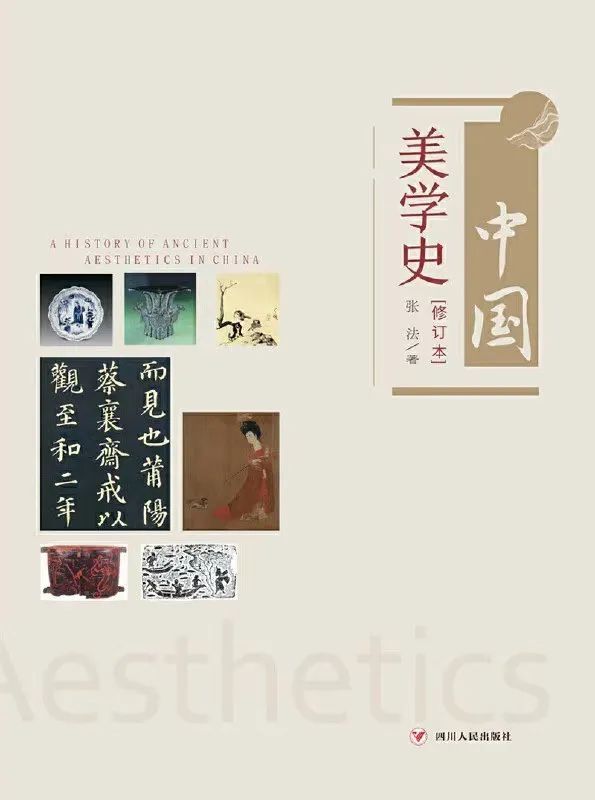
吕东:确实,如何提升中国美学,一直是中国学人努力在做的事。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更为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对于美学来讲,您认为当代学人应当做怎样的努力才能更好地推动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呢?
张法教授:三大体系建设,对于美学来讲,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但较之其他学科,又要困难一些。美,从理论上讲,非常复杂。且以中外学人都熟知的三个命题来谈吧。看见一朵圆形的红花,说花是圆的,别人必须承认“是的”,不然就错了。说花是红的,别人也必须承认,不然就错了。但若说花是美的,有人就可以说不美,你却不能说他错,至多说他的审美与你不同。正如当年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所写的那样:试图找出美的本质,经过不断追寻,对别人提出的命题一个个地否定,而最后仅能以一句哀叹结束——美是难的。虽难,但一千多年后,西方终于在18世纪建立起学科型美学,并影响了世界的美学演进。如今,在西方美学的升级以及世界美学的多元互动中,中国美学有了更好的基础,三大体系建设应是中国美学在新时代进行提升的方向。虽然困难很多,但相信中国当代美学学人凭借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丰富经验,应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和世界美学的召唤中有所作为。(文/吕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哲学动态》2022年第10期)
美学家简介

张法,男,毕业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博导,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教30多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年度),第六届、第七届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2008—)。主要研究美学与思想史,独著有《美学导论》等22部,合著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论》等5部,主编有《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9(艺术学卷)》等6部。马工程教材《中国美学史》首席专家(主编)、《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等4部著作入选国家级外译项目(英语,俄语)。独著《中国美学史》《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有韩文版,文章300多篇,16篇为《新华文摘》转载,12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美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