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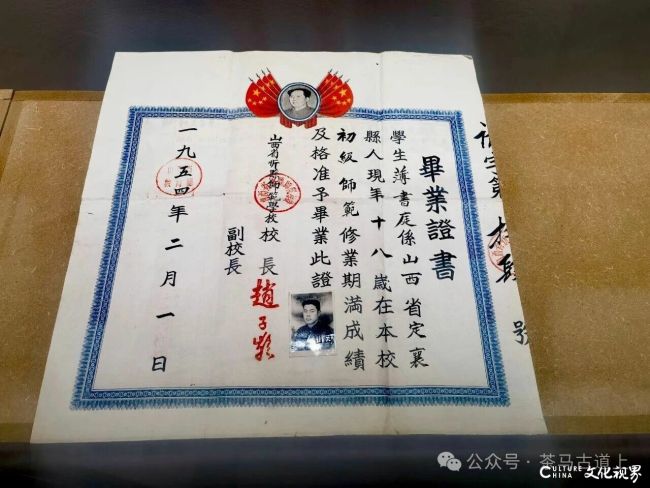
清代忻州学者薛河东、赵宗先等皆在此讲学,他们编纂地方文献、整理元好问遗作,使“遗山学风”得以延续。

书院山长廊庑间悬挂的元好问诗碑,便是对学子最深沉的精神召唤。作为清代忻州最高学府,书院三百年间培育了数以千计的秀才、举人、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忻州人才。

舒建新从城堡学府回来了,我问他咋去这么久,他说:“迷路了,这座城堡似的学府太令我震撼了,从建筑学的角度讲:书院依山势构建的攀登之姿,本身就是对学子最深刻的教诲之意;我仔细考察:发现从山门至顶峰三台(象征“状元、榜眼、探花”),需攀爬六十级石阶。学子每日拾级而上,身体力行地体验‘书山有路勤为径’的艰辛。讲堂位于中台,藏书楼高踞顶台这个巧妙的设计分明告诉学子——知识需逐步求索,而智慧终须登高望远。这种建筑语言,比任何训导都更直抵人心,并把深刻的学理隐喻在建筑设计之中,太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