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海”与“石”褪去物象的外衣,当“空白”成为能量的居所,水墨完成了从再现到生成的蜕变
杜小同,这位从学院写实教育体系走来的艺术家在中国画的时空观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他的艺术之旅是一场漫长的“去伪存真”。
在浙江美术馆的同名个展中,他将近年来的探索凝练为极简的空间诗学:笔墨退隐,空白发声。这是一场关于视觉的减法,却是一次感知的加法。在这里,我们看不见海,看不见石,却能感知到空间本身的低语与呼吸。
杜小同的艺术之路始于一个看似标准化的学院起点:学院写实教育。石膏像、透视、光影——这套理性、直接、可控的语言,塑造了这位70后最初的观察方法与工作逻辑。1995年,当他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杜小同接触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那种注重造型和色彩的直接表达方式曾给他带来表达的快感,那种层层塑造,即时反馈的掌控感,与水墨的“慢”与“隐”形成了鲜明对比。水墨要求他放下既有的观察习惯,去理解“骨法用笔”、“应物象形”背后的哲学意味,去体悟“计白当黑”中的空间智慧。这不仅是技法的转换,更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重塑。

《叠石之五》237×124cm水墨宣纸2023
“唯有深入一个系统,才能真正懂得如何走出它。”正是这种在两种视觉经验间穿行的背景,成为他艺术生涯最宝贵的馈赠,它让杜小同始终对任何固化范式保持着清醒与警惕,既不满足于学院教育的客观再现,也不轻易沉溺于文人画的审美惰性。怀疑、不满足,由此成为他创作中最核心的驱动力。
物象的退场
“海”是杜小同最为人熟知的题材,但这并非一蹴而就。在烟台生活十余年后,大海才从他眼中的风景,逐渐升华为精神的场域和空间的隐喻。到2020年前后,他的海景作品在语言上已日趋成熟。
然而,杜小同却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太完善了,反而失去了绘画的感觉。”他敏锐地察觉到,当“海”成为一张被完美描绘的“风景画”时,它的本质反而被遮蔽了。风景成了阻碍。

《岸二》52×90cm水墨宣纸2022
于是,杜小同转向“竹石”——这一最传统、也最符号化的文人画题材。但他画的并非文人赏玩的“瘦、漏、透”之石,而是野性的、无名的“顽石”。他不断地实验,甚至将“竹”从画面中彻底剔除,只留下石头本身。接着,他通过覆盖、涂抹、淡化,让石头也逐渐隐退。

《挨着的两块石头》145×365cm水墨宣纸2022
空间的觉悟
这场漫长的退隐,最终将杜小同引向了对“空间”的终极觉悟。只有当形象退让,空间才能说话。他逐渐意识到“空间本身即是一种表达”。“我要构建的是一个有巨大能量的空间,而不是画什么东西。”这一认知让他走向了极简。
但杜小同强调,这并非源自西方极简主义的影响,而是从中国画内部生长出来的逻辑,可以追溯至他对中国画“时空一体”本质的体悟。他不再将笔墨视为描绘物象的工具,而是理解为构建时空关系的“动作”。古人画兰,一撇一捺,既是时间的流淌,也是空间的分割;书法的提按顿挫,既是节奏的韵律,也是气脉的贯通。他意识到,这种将时间凝固于空间、让空间因时间而活化的能力,才是中国画真正的“基因”,而非那些被反复临摹的皴法或图式。他所做的,正是将这种基因从具体的题材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绘画的本体。
为了保证空间的纯粹性,他开始有意识地清除一切可能干扰空间自主性的“杂质”。他不再钤盖印章,因为那枚小小的红色图章,承载了太多文人画的身份认同。他甚至将签名简化为一个“同”字,让它仅仅只成为一个标记,一个存在的证明,而非一个需要被欣赏的书法元素。他希望观众面对的,是画面本身,是那个由空白与笔触共同构成的、独立自足的世界。

《c大调之七》182×145.5cm纸本水墨2025
在浙江美术馆的同名个展中,杜小同将这种“克制”的哲学贯彻到了展陈的每一个细节。他与策展人杨大伟反复商讨,不断删减作品,最终只保留那些最能说明核心问题的画作。在他看来,展览不是作品的堆砌,而应像他的画作一样,通过有限的画面,直指一个根本性问题。
展厅几乎没有任何冗余的信息,简洁、寂静,观者的体验也随之改变。站在杜小同的画前,我们不再是“看画”,而是“进入”一个被精心构建的知觉场。我们无法快速地辨认出“这是什么”,从而获得一种认知上的满足感。相反,我们被邀请去“感受”——感受那片空白的“重”,感受那抹墨迹的“轻”,感受形象与空白之间那微妙的、如同呼吸般的张力。画中的“覆盖”与“消隐”,不再是技术的炫示,而是一种引导,它迫使我们的视线在“有”与“无”之间徘徊,在“显现”与“遮蔽”之间思考。
在这里,“写实”不再意味着复制,而是忠实于感受的真实性。正如塞尚怀疑自己的每一笔,却在怀疑中不断靠近“世界如何显现”的真理,杜小同的不满足,也让他不断回到“白纸”的张力之中。他让我们看到,不是石,不是海,而是存在如何在空间里生成。


“杜小同”展览现场,浙江美术馆(杭州),2025
当海与石褪去物象外衣,当空白成为能量的居所,水墨完成了从“再现”到“生成”的蜕变。最终,杜小同走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哲学命题:人如何通过绘画这种古老的行为,与世界重建一种本真的、深刻的联系。
站在他的画前,我们看不到风景,读不到故事,却感知到一种广阔的寂静——那是物我交融的时空,是身体与空间的共振。杜小同用极少的笔墨,让我们明白:艺术的本质,是让“看得见”与“看不见”同时发生。

《此山》145×365cm水墨宣纸2022
展览是艺术讨论的起点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为何这次展览没有取标题?而是直接用自己的名字?
杜小同(以下简写为杜):这次展览题目是和策展人杨大伟共同商定的。之前我在广东美术馆的个展叫“天高云淡”,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叫“寥”,还有策展人孙欣也曾以“无际”为我的展览命名。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策展人和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从我的作品中读出了某种对空间的叙述。这些展览标题中似乎都蕴含着一种时空观念,这说明观众确实能从画中感受到这种维度。
这次和杨大伟深入交流时,我们也谈到了近年来我对空间的思考与实践。最后他提议,不如就回归最本质的呈现,不以概念先行,直接使用“杜小同”这个名字。我觉得这样很好,不给观众先入为主的指引。没有预设的阐释框架,观众反而能更直接地面对作品。当人们站在画前,不再只是简单地识别“这是海景”或“这是石头”,而是不得不思考:这幅画到底表达了什么?这种被迫的思考,恰恰是我认为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

“杜小同”展览现场,浙江美术馆(杭州),2025
Hi:这个展览算是对你艺术生涯的一次回顾吗?与以往的个展有何不同?是否有特别的考量?
杜:更像是近期探索的实验性呈现。本次展览也与之前的个展很不一样,可以说是我转型阶段的一次集中展示,基本上都是用近年来的新作品构成的。展出的作品大多创作于2019年之后,其中至少一半是首次展出,之前从未参加过任何展览。虽然也有少量较早的作品,但都是为这次展览特别挑选的,用来呈现一条清晰的创作线索——尤其是在杭州这样一个注重传统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这条线索,更好地理解我的思考轨迹。

《兰系列之一》126×50cm纸本水墨2024


《兰系列之二》126×50cm纸本水墨2024
HI:你希望观众在看完展览后,对“杜小同”这三个字形成怎样的理解?
杜: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不同,有些观众的感受力会更敏锐一些。我并不希望自己被理解成某种非常具体的东西或形象。我更期待的是,观众在面对作品时能持续地感受和思考,最终体验到一种巨大的空间性存在——或许是一种能量,又或是一种力量。
哪怕只有一点点这样的体会,我觉得就足够了。展览的真正意义在于作品与观众之间的直接沟通。新作品可能会让一些观众感到陌生,甚至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转变,也可能会引发一些不解或质疑。但我觉得,展览就应该成为艺术讨论的起点,而不是简单地展示已知的东西。如果我还在画过去的那种风景画,停留在原来的状态,那不是我。艺术家的创作会有变化,这是很自然的事。

“杜小同”展览现场,浙江美术馆(杭州),2025
Hi:展览海报上的“杜小同”是你自己题写的吗?听说你从小就很喜欢书法,书法的练习对你的水墨创作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杜:是的,海报上的字是我自己写的。我从小就对书法有种天然的喜欢,没人教。就是偶然看到字帖觉得太美了,就拿回来自己照着写。这是一种本能的吸引。
其实最初选择国画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书法。在附中时我们受的是西画训练,周围同学大多选择油画、版画,当时还有人劝我学设计,说学油画可能不好找工作。但我对那些实用性的方向兴趣不大,内心还是想追求纯粹的艺术表达。
在我看来,书法早已脱离了原有的文化土壤,就像传统绘画一样,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早已发生变化,不可能真正回到过去了。但书法本质上是一种痕迹,就像我们研究上万年前的岩画——透过笔触和结构,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唐人的书法、魏晋的风度、明代的姿态,其实都是不同时代社会关系、生产力水平和人的观念变化的反映。
所以我认为,书法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种人与世界的观念对应。如果只停留在技巧层面,写得再漂亮,也只是一个“书法的样子”,是表面的,甚至是一种“伪书法”。真正有价值的书法,是透过笔墨传递出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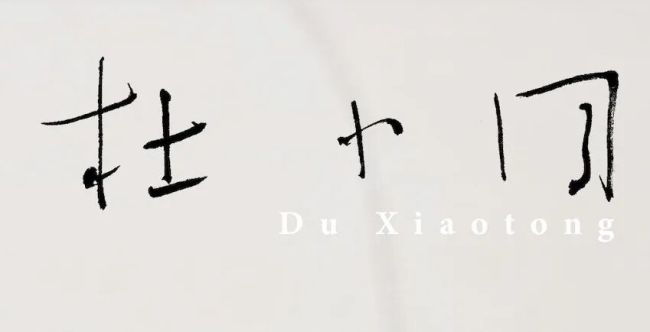
“杜小同”展览海报局部
Hi:你曾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渗透于时间的观念”,并认为“中国画自然跟时间是最紧密的,最贴合的”,能否深入阐释你对时间与水墨艺术关系的理解?这种时间观念如何体现在你的具体作品中?
杜:其实在中国画里,时空是一体的。比如我画海,不仅仅是在处理空间,更是在呈现时间的流动。我创作一张画的过程本身就有很强的时间性——比如画一根线,可能要反复画上十五六遍甚至二十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单看画一根线可能不需要多少时间,但我是非常缓慢地推进。更重要的是,我每天都会反复审视画面空间,不断揣摩和调整。这种日复一日的累积和沉淀,本身就是一种时间的体现,也会在作品中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张力。
其次,中国画本身的线条就带有时间性。无论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还是从右到左,用笔的方向和节奏都暗示着空间的延伸和时间的流动。如果你对传统艺术敏感,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书法的时序性更加明显,每一笔都有先后,不可逆转。
中国艺术,尤其是书法和古琴,时间性比西方艺术更突出。西方可能更注重空间的构建,而中国艺术则更强调时间的展开和过程的体验。这种时间性,是中国传统艺术非常核心的一个特质。

《变奏》183×145cm纸本水墨2025
Hi:你的许多画作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在视觉上,它们往往是轻盈、空灵、透气甚至是朦胧的;但观者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寂静、孤独、时间的流逝乃至生命的哲思。你是如何有意识地运用水墨的特性,通过这种视觉上的“轻”来承载和表达内涵上的“重”的?
杜:这倒不是刻意为之。如果你能看出这一点,说明你真正走进了这些作品。这正是我希望传达的——虽然每件作品未必能完全实现我的想法,但我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之所以逐渐淡化甚至去掉风景的具象元素,就是因为觉得“风景”本身会削弱我想表达的东西。它像一层遮蔽,让我真正想呈现的东西被掩盖了。这种追求其实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审美向来推崇“空灵”、“飘逸”和“远”的境界。而这些境界其实是“去伪存真”的过程所带来的感受,就像卸下慢慢堆砌的身份角色,与自我面面相觑所带来的陌生感。现实是浑浊的,需要被提炼、转化,笔墨才能干净起来,才能达到那种“飘然”的状态。
“远”,不仅仅是一种空间距离,更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的距离。人类骨子里有着对“真”和“实”的渴求,无论是哲学、科学、艺术都是对其追求的不同路径。在路途当中我们会迷醉于折射光的璀璨,但天性会让我们不满足于片段的真相,驱使我们不断的自我审视,校正,抛下熟稔,在过程中燃烧掉粗重的外壳,换得轻盈的瞬间,继续奋而触摸。

《皆是》228×558cm纸本水墨2024
Hi:你曾强调“我是一个非常写实的画家”,这与观众从你画面中感受到的朦胧、诗意和表现性似乎有些不同。你能具体谈谈你所理解的“写实”吗?
杜:当我画那些海景系列作品时,之所以称自己“写实”,是基于学院训练带给我的理解。写实训练的本质是培养艺术家与对象之间的表现能力——如何充分而准确地传达你所见的对象。这是我们学习绘画的基本课题。
我对写生的看法也是如此。当我面对一片海,或任何自然景观时,任何夸张、变形或扭曲的处理,在我看来是因为没有感受到对象的内在,才需要借助这种“表演”来假装感受。
因此我认为,像梵高这样的画家,本质上也是写实的。因为他笔下的世界就是他真实看到的世界——他不是在故意变形,而是忠实地表达他的视觉体验。如果是有意的风格化,那么画一张就够了,不可能每张画都保持同样的强烈表现力。我把这种创作方式称为“写实”,因为它真正尊重艺术家的感受,忠于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这才是绘画的真实性。如果背离了这一点,任何表现都只是假象和表演。我相信如果观众站在我的角度,也会看到同样的海。我很少去刻意夸张,或者假装某种表现性。我画的海,就是我所看到的海的样子。

《岸》72×100cm水墨宣纸2022
Hi:能否谈谈你的创作过程,你需要写生吗?
杜:我很少写生。因为我的创作不需要通过写生来实现。无论是画海还是其他题材,我更倾向于依靠内心的感受和想象来直接作画。以前画人物时也是如此。
我不喜欢先画一个东西,再把它转移到画面上。如果已经画过一遍,为什么还要再画一次?我的绘画的兴趣就没了。我的方式是直接面对画纸,笔墨直接在画面上实现,不需要参考照片或其他图像资料。参照图片或者直接写生都会干扰我。


杜小同画室
水墨必须与时代对话
Hi:你如何看待“新水墨”或“当代水墨”这样的概念?
杜:说实话,我不太清楚这些概念具体是谁提出的,也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说法很多年前就出现了,甚至有人把吴冠中先生也归入“新水墨”的范畴,大概是因为他的作品与传统国画很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些标签并不确切。叫“当代水墨”也好,其他什么名称也罢,其实并不重要。关键不在于你属于什么流派,而在于你的作画逻辑和思维方式,在于你如何思考和工作。名称本身解决不了问题。
Hi:那你认为在当代,水墨艺术最独特的价值和挑战是什么?
杜:中国传统绘画体系非常完整、稳定,但也非常沉重。它有着深厚的传统包袱,这是我们的文化根基,但同时也带来挑战。为什么日本和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发展出像“物派”或“单色绘画”那样具有现代性的艺术形态,而中国没有。可能因为他们是儒家文化圈的边缘,反而更容易轻装上阵。
中国画体系太完备了,所以要实现现代转型需要更长时间的消化和突破。但我认为这个转型是必然的。如果传统不进入现代性,它就失去了生命力。艺术必须尊重身体并保持开放的状态。必须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和整理,才能产生新的价值。
Hi:本次展览之后,是否有新的创作计划或探索方向可以与我们分享?
杜:暂时不会有太大的转变。现有的两个创作方向——海和石——还需要继续深入。展览是审视自己的机会,只有在展厅里看到作品的整体呈现,才能真正检讨自己的创作。
我会继续推进现有的探索。当然也可能会有新的题材出现。题材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它们能为我提供构建空间能量的基础,让我的艺术语言更深入。不同的题材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和重新打开的可能。

(来源:Hi艺术 沈冀星)
画家简介

杜小同,1972年生于陕西富平,1995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附中,199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水墨人物画室获学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获艺术硕士学位,现就职于江苏省国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