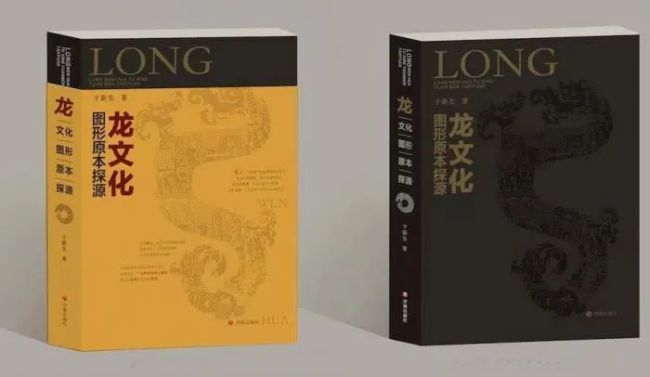
对于龙起源的问题,有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和探讨,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龙原形说,大多数观点认为:龙,起源于某种动物或自然现象。其代表性的观点有:认为龙是由蛇图腾兼并了其他图腾而来;认为龙是蛇的神秘化;认为鳄鱼的形象和习性接近于龙;认为龙源于闪电;认为龙源于云;认为虹是龙的原形;认为龙是树神的化身;认为龙源于猪等等。针对龙的起源,于新生的《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一书则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观点,该书打破先前的研究理念及方式,以原始思维作用下的原始图形形成元素及造型方式为依据,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析了龙文化的起源及其衍化的原本特征,具有前所未有的学术开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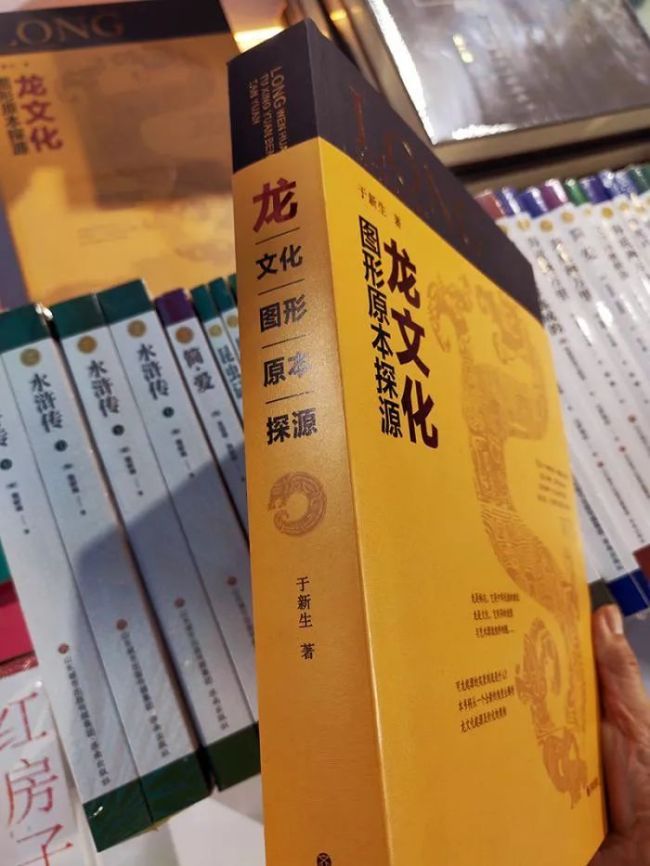
该书的研究方式和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以图形造型方式参与古文化图形研究的“图形还原法”
当历史成为遥远的过去,人们不可能再回到以前去看古代的真实,但古代却留下了许多的线索和信息,让人们作为依据去探索古文化的奥秘。在这些线索和信息中,古人物化在材料上的图形文化是研究古文化最为可靠的实物依据(种类有:绘画、雕塑、建筑、工具、器皿、服饰、文字、符号等)。相较于语音文化和行为文化,只有图形文化才具有恒久性,它要比后人的记载和传说更为真实可信。龙图形同样是以图形的形态流传并保存下来的。图形文化的形成须有四方面的因素:1.当时社会的思维形态;2.图形产生的原本元素;3.图形产生的造型方式;4.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及物化这些图形的工艺与材料。原始图形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扑朔离迷的神秘复杂现象,也正是在原始思维作用下,图形的原本元素通过不同的图形造型方式物化在材料上来体现的,而图形的造型方式更是直接关联着图形形成的特征。这些图形的造型方式既有类似造字“六法”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也有表现事物的综合意象(包括表现视觉不可见的物象内部特征)、夸张与省略、平面移位、异物构合、为神灵造型(包括把物象具有神性的部分神灵化)、以意为象、形随意出、集形表意等多种方式。如果不了解这些造型方式,仅是从“象形”的角度去解释那些神秘的古文化图形,是难以找到其图形原本成因的。这也即是《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一书将图形造型方式纳入古文化图形研究的原因。“图形还原法”针对古代遗存以图形文化为存在形式的特点,不局限于考据材料与考证对象的表象直接对应,而是通过了解原始时期的思维方式、图形产生的原本元素、图形的造型方式及工艺材料与原始图形的关系,在考古发现和其它可用材料的基础上,以原始思维为背景,把已知的古代文献及出土文物等实证材料带入到由原始思维形态形成的图形造型方式中去,分析图形的生成过程,从而还原古文化图形生成的原本。
二.提出“原本思维”和“原本艺术”的概念
《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一书认为原始美术的思维方式、造型方式与民间美术的思维方式、造型方式有相类相通之处。民间美术是原始美术的自然延续,从民间美术中可看到其保留了大量的与原始思维形态及造型特征相类同的艺术形式。这些原始美术造型方式在民间美术中的形态延续和遗存,同样体现了人类思维及艺术形态的原本性特征。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文化形态差异的重要因素,而思维方式的类同也必然会带来文化形态的类同,正是由于原始美术与民间美术在思维方式及造型方式上的类同性,从而也就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产生了依据。该书将不同时期延续并保持了原始思维特征的思维方式统称为“原本思维”,将原本思维下产生的原始艺术、民间艺术等形态统称为“原本艺术”。“原本思维”和“原本艺术”概念的提出,其用意在于削弱因原始艺术时间概念与民间艺术范围概念所形成的隔离,强化其形态的共性特征,以利于在原始图形的研究中对龙起源及其他原始图形的解读提供更多的现存参照和启示。
三.提出古文化图形研究的的“四重证据法”
鉴于民间美术对原始美术某些信息的保留及其造型方式的类同性,《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一书将民间美术作为原始美术造型方式的延续形态来参与古文化图形的研究,特提出以古文化图形的造型方式为形成依据,并以民间美术参与古文化图形佐证的“四重证据法”。这就在以往“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以历史实物、记载、传说参证的基础上,增加了将美术学中的图形造型方式介入古文化图形分析并以民间美术这类当今实物参证的可能性,从而为古文化研究提供了第四重证据。此参证方式可从三个方面为古文化研究提供证据参考:一是古文化图形是由图形造型方式形成的,对古文化图形原本的探究,也必然要以其造型方式为研究依据;二是某些民间美术形态仍然延续并保留了古老的原始文化信息,可与原始文化相互印证;三是由于原始美术与民间美术在造型方式上均具有原本特征的类同性,可依此作为原始美术造型方式的参照介入古文化图形的研究。此种研究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古代的原始资料的直观层面,而是通过分析图形的造型方式并利用文化积淀的现实形态(民间美术、民俗文化等)来参与揭示古文化的原本形态,相对于传统考据学直接实证对应的方式,为探讨古文化图形的形成从造型上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及更多的参证依据。
四.创立龙原形起源于原始生殖崇拜的“肠龙说”
“肠龙说”是《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一书由以上方式研究龙起源的主要观点。早期的龙造型多由不同物类的头部与相似的弯曲条带状身体两部分构成,就原始龙纹头部的不同特征来看,其并无源于某一物种再衍化到其他物种的相互联系,且同时期的龙造型头部也不尽相同(如红山文化玉龙),因而该书认为:不同类型龙的头部各不相同,其显现出来的是龙的个性特征(不同物类及不同部族图腾物);不同类型的龙所呈现的共有的弯曲条带状身体,显现出来的才是其崇拜内容的共性特征。龙与龙之间的头部不同与身体的相似,说明龙是由不同物种、不同图腾部族(头部)与相同崇拜内容(体部)结合而成的。以此切入,本书突破以往仅从“象形”角度在动物或自然现象中寻找龙原形的观点,而是通过古文化图形造型方式的介入来对龙图形进行研究,认为龙的原形物并非起源于某种完整动物或自然现象,而是源于原始生殖崇拜中人们认为生命体中所具有生殖神性的某个部分,这个被认为具有生殖神性的部分,即是所有动物都共有的“肠”。原始生殖崇拜对“肠”生殖的认识,就像古人感性地认为“心”是主管思维的器官一样,由于生命是在腹中之肠的包绕中孕育,更因生命在分娩时与肠形脐带相连,故而在对生命孕育还处于感性认知的原始思维中,肠也就被直观地看作是生命的生殖之源。基于这种感性的认识,肠在原始生殖崇拜中便成为了极具灵性的生殖神物。在对此生殖神物进行神灵化的图形造型中,人们以“拟人”“拟动物”的方式赋予了肠想象中的神灵特征:先是给肠加首,后又给肠长足、添翼、生角,并逐渐添加其概念所需的诸多象征符号,从而以“集形表意”的造型方式使肠成为了一种具有动物化特征的灵物:龙。龙图形的形成及其所体现出的动物性造型,正是人们在原始思维中用艺术造型的方式将肠神灵化的结果。《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一书依据原本思维方式和原本艺术的造型方法分析了龙图形的形成过程。从原始龙图形的造型特征、古“龙”字的形态、天干“己”与肠的关系及在人身的相应定位、“女娲之肠”的神话传说、蟠龙纹围绕孕子的造型原本、古代文物中的肠纹认定、龙的造型演化及类型、龙与相似物的“互渗”、民间风俗遗存与龙的联系等为依据,并对赵宝沟文化尊形器神灵物图形、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蚌壳摆塑、“肠孕子”“龙孕子”“蛇孕子”与“蛇盘兔”图形、曾侯乙墓漆棺纹饰、《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马王堆汉墓帛画》、《金雀山汉墓帛画》、“黄肠题凑”的古代葬制、董家庄汉画像石墓立柱图像等肠龙生殖图形个案进行解析,还原证明了原始生殖崇拜中人们认为的生殖神灵“肠”即是龙的原形。以此解释了原始龙紋头部的多物类特征及在原始生殖崇拜中涵盖所有生殖对象的广泛性、包容性及由此而来的祖先神、自然神、王权神等概念的延伸,体现了龙原形在原始生殖崇拜中其个性特征与共性意义的合理性。
五.根据龙的不同特征和属性,对龙的类型进行新的归纳和划分
从不同时期发现的龙图形特征来看,其既反映出了不同地域、不同部族龙崇拜的差异性,也反映出了龙崇拜由社会共性追求所带来的一致性。根据龙的造型特征及象征内容,《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将其归纳为个性龙和共性龙两大类型。个性龙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氏族、不同崇拜对象、不同物类特性、不同功用、不同造型特征等因素所产生的具有个性特征的龙。据时期可分为原始个性龙和后期个性龙,据造型特征又可分为龙体个性龙、龙首个性龙和变体个性龙。除个性龙外,人们还相信天下有一个统一所有物类的龙,它是天下万物共同的生殖之神,这就是龙观念生成后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化完善的共性龙。龙的种类除以上个性龙和共性龙的划分外,还可据其不同属性划分为五类:圣龙,神龙,天龙,子龙,物龙。这五类龙又可归为两大类:神化龙和现实龙。圣龙、神龙、天龙、子龙为神化龙;物龙为现实龙(现实中的似龙动物及现象,其实质并不是龙)。虽然这五种不同属性的龙在概念上有时也有一定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但其大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对龙属性的区分在龙文化研究中十分必要,如果不加区别,就会在认识龙的过程中产生矛盾和混乱,使龙一会儿至高无上,让人奉为神明,一会儿又作恶多端,被人斗杀。厘清龙在属性上的区别,有助于在龙文化研究中把握龙的不同本质和内涵。
六.依据原始思维“互渗律”来解释龙与相关物象的“互渗”现象及其与龙的区别
原始思维用“互渗律”来认识解释事物,认为宇宙万物在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神秘的联系,某些具有类似特征的事物常被视为同类。当龙崇拜出现后,一些形状或特征与龙相似的物象就极容易与其产生“互渗”,这便使龙产生了诸多的派生物,从而也造成了其概念的不断扩大。如:因与龙体原形“肠”的相似,产生了龙同蛇、虺、蚓、蚕、绳、带、藤等似肠物象的“互渗”。又因生殖神概念与天地的联系,产生了与龙形相似的雷电、云、虹、河流等自然现象的“互渗”。后又因神灵化(动物化)的龙形象与某些动物外形的相似,进而产生了龙与鳄等似龙动物的“互渗”等。也正是由于这些物象与龙的“互渗”,从而形成了后人对龙原形的种种猜想及龙起源的不同说法,但这些龙的“互渗”物均是在龙概念形成后延伸排生出来的,并非是龙的最初原形。
七.对与生殖崇拜相关的其他古文化图形进行解析
《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在对龙图形的象征内涵、造型方式进行解读后,进而又对与生殖崇拜相关的其他古文化图形进行分析。并对一些类型化的古文化图形辟专章进行探讨。如:1.以图形还原法证明了由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图形、龙山文化兽面神徽、夏代兽面铜牌饰、商周青铜礼器兽面纹、汉代及之后的铺首等所呈现的兽面图形,并非仅是对兽面形象的表面描绘,更非食人的饕餮,而是在原始生殖崇拜作用下,以图形造型方式对“腹”(生命的孕育、保护之宫)神灵化后所表现的祖先神、保护神之象征。青铜礼器上所谓的“虎食人”图形也非食人,而是“生人”“护人”之意。还证明了鼓的出现同样是由腹神崇拜而产生的祖先神、保护神之象征。2.还原了由卵崇拜而来的卵纹与日、月、璧、珠、乳钉纹、籽纹、卵化纹、太阳鸟、朱雀、凤凰、鹏、太极图等的衍化关系。3.还原了由蛙崇拜而来的马家窑文化变体蛙纹的原本,证明了其是由图形造型方式所表现的由蛙卵→蝌蚪→幼蛙→成蛙生长过程的综合图形,并探讨了蛙崇拜与母祖、月神、蝌蚪纹、子、娃等图形的联系。还辟专题对“履大迹”传说、与“履大迹”相类似的纳斯卡地画的制作方式及制作过程、仰韶文化人面鱼纹、龙首上的“且”纹与“辛”纹、殷墟妇好墓跽坐玉人像柄形器、三星堆突目大耳青铜面具造型、鬼脸钱造型、古代货币的生殖象征、曾侯乙墓出土漆箱图像等进行了个案解析,就一些学术界关注的古代文化图形解读提出了全新的看法。
八.解读古文化图形象征符号的内涵及组合方式
象征符号是古文化图形形成的基本元素。这些符号与古代社会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崇拜对象及心理追求密切相关,它们在古文化图形中的运用,多数并非是出于单纯的装饰目的,而是源于原本思维对事物认识所赋予的特定象征意义,正是这些程式化神秘符号“集形表意”的组合,才形成并体现了古文化图形的特征和内涵。《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一书根据这些符号在图形中的特征,从其本质和形态上进行归纳、定义、命名,将其分为六大类:1.生殖之门,包括:儿纹、半儿纹、公纹、蒂纹、贝纹等。2.交合之纹,包括:缠绕交合纹、相对交合纹、勾连交合纹、衔咬交合纹、共体交合纹、穿插交合纹、叠合交合纹等。3.生命之树,包括:生纹、勿纹、枝叶纹、肢爪纹等。4.繁衍之子,包括:子纹、刀羽纹、鳞纹、籽纹等。5.标识之冠,包括:冠纹、角纹等。6.谐音之图,包括:音借、义借、音义双借等。了解这些符号的含义及组合方式并将其明晰化,对于解读古文化图形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也使诸多过去不明其意的古文化图形得到了解读。
九.归纳中国古代生殖崇拜图式的基础内容
《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一书通过对中国古代生殖崇拜内容及其图形造型的分析归纳,认为肠(龙)崇拜、腹崇拜、卵崇拜、受孕崇拜、蛙崇拜、生殖器崇拜、树崇拜、阴阳交合崇拜为中国生殖崇拜图式的基础内容。这些内容包含了古人认识生殖的多个方面:肠(龙)崇拜,是生殖神;腹崇拜,是孕育、保护神;卵崇拜,是生命原本和生殖对象;蛙崇拜,是生殖母祖及生殖之子(以蛙谐娃);受孕崇拜,是生殖的外在因素;生殖器崇拜,是生殖器官和生殖通道;树崇拜,是氏族生殖繁衍的象征;阴阳交合崇拜,是生殖的条件。依此内容为基础与其他物象的“互渗”,又延伸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图形。
这些生殖崇拜内容的衍化图形为:
肠(龙)崇拜延伸图形:龙、伏羲、女娲、蛇、虺、蚓、蚕、玄武、绳、带、藤、雷电、云、虹、河流等。
腹崇拜延伸图形:神人兽面像、兽面纹、虎、狮、铺首、鼓、白虎、西王母等。
卵崇拜延伸图形:日、月、璧、珠、乳钉纹、籽纹、卵化纹、太阳鸟、朱雀、凤凰、鹏、太极图等。
蛙崇拜延伸图形:母祖、月神、变体蛙纹、蝌蚪纹、子、娃等。
受孕崇拜延伸图形:图腾物(玄鸟等)、受孕神灵(交合神兽、麒麟送子等)、自然受孕物(月、星、虹、卵等)、祭祀生殖偶像、佩挂生殖偶像、触摸生殖偶像等。
生殖器崇拜延伸图形:男根、且(祖)、图腾柱、女阴、贝纹、儿纹、半儿纹、公纹、蒂纹、柿蒂纹等。
树崇拜延伸图形:生命树(社木)、扶桑、生纹、勿纹、支纹、枝叶纹、肢爪纹、刀羽纹、鳞纹等。
阴阳交合崇拜延伸图形:两仪、天地、日月、龙凤、魂魄、缠绕交合纹、相对交合纹、勾连交合纹、衔咬交合纹、共体交合纹、穿插交合纹、叠合交合纹、太极图等。
由此对中国古代生殖崇拜图式基础内容的明晰化,可看出在中国古文化图形中生殖崇拜图式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体现了古代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对生命探索及认知的各个方面,而龙则是这个庞大体系中的典型代表,它的形成和完善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见证和象征。
《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是一部系统的以美术学图形造型方式参与古文化图形研究的学术著作,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拓性学术意义。该书以大量的古文化图形为依据,并通过图形造型方式对原始文化图形的归纳、分析、研究,不仅创立了龙起源的“肠龙说”,还解析还原了其他诸多古文化图形的原本内涵,使其脉络有机的联系起来。这些探索为古文化图形的解读打开了一扇新的门,其必将会对后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文/启迪,来源:大美墨韵)
作者简介

于新生,1956年8月生于寿光,1988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第六届副主席,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书画学会学术委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正高二级),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99中国百杰画家,中国文联第三届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全国第七次文代会代表,中国国家画院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入选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