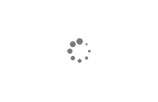内容提要:本文提出应该高度重视石窟寺艺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本文对以往石窟寺艺术的研究队伍和基本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之后,以2023年7月在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召开的“再造像——当代文化视阈中的石窟艺术”研讨会为例,介绍艺术家群体在介入石窟寺艺术研究之后,在方法论上所带来的新气象;同时,通过近些年来高新科技越来越多地介入石窟寺研究的现象,展望了石窟寺艺术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未来趋势。
一
石窟寺艺术近些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彰显,得到了社会各界和美术院校的高度关注。在美术院校,石窟寺艺术考察成为了学生的必修课,也成为一部分本科生、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石窟寺艺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石窟寺艺术?如何形成关于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已经成为今天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石窟寺艺术和佛造像的研究面对的是历史。历史学常说,关于历史的研究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的研究,这是要搞清楚历史的客观事实,历史的真实存在是什么怎样的?另一个是价值的研究,就是要解释,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那么,什么是石窟寺研究的方法呢?方法就是为了解决石窟寺艺术的事实和价值这两大问题,所采用的手段、途径和方式。方法论则是关于这些研究方法的理论。
二
石窟寺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群体,各个群体在方法论上各有侧重。
第一、石窟寺考古学的方法。
石窟寺考古学是北京大学宿白先生开创的。宿白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就自觉地将考古学运用到石窟寺研究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其后,石窟寺考古学开枝散叶,目前成为石窟寺研究方面最具有学科体系和方法论意识的研究学派。
石窟寺考古学注重事实研究,它按照科学的、理性的方法,来客观地记录、勘察石窟寺的基本事实。首先它通过细致、客观的记录,力求弄清石窟寺的年代;做好排序、分期、分段工作;然后把石窟寺的每一个平面、立面上的遗留的痕迹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强调完整、客观的态度、不带主观偏见地还原历史现场;除此,它还要开展对石窟寺的整体和周边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考察地形、山势、道路交通、土壤、石质、含水量、开凿的工程量等各个要素;还要考察石窟寺所在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信仰等综合情况,以及与周边村镇的关系。总之,石窟寺考古学的目标就是把石窟寺得真实事实呈现出来。
所谓石窟寺考古学最有价值的,是为进一步展开石窟寺研究提供事实基础。正因为石窟寺考古学的严谨、客观的方法以及言必有据的态度,所以它常常跟从事艺术史研究的,特别是跟艺术家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强调用事实说话,不接受主观的推测、估计和想象。所以,过去石窟寺考古学的研究者不太能和艺术史家、艺术家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可能就会吵架。
第二、文博系统专家的基本方法。
实际上,文博系统专家的研究跟美院美术史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他们之间存在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第一、文博系统的专家相对于美术史家,他们会更重视事实的资料,特别是考古学现场的实物材料。第二、文博系统的专家与做美术研究的专家相比,他们的关注点有差异,表现在研究方法上,文博系统专家的关注点相对比较综合、比较全面;例如更重视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文献学、文字学等方法;美术史专家也强调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但是由于所在专业的原因,他们更重视美学和视觉文化,重视图像学、风格学、造型学的方法。当然,这种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很多时候,文博系统专家和艺术史研究的专家在某些课题的研究中,看不出在方法论上有多大的差别。
第三、艺术史学者的研究方法。
艺术史上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在今天看来,也是源远流长。像西安美院的王子云老师;中国美院的史岩老师;中央美院的金维诺老师等等,他们是美术学院研究石窟寺艺术的前辈,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学生。
例如中国美院的史岩老师,他早在1943年就担任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在敦煌莫高窟,他点着蜡烛在幽暗的洞窟抄录画像题记,在敦煌抄录了109个洞窟,940条供养画题记,他的研究成果《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1947年出版后,直到今天,仍然是研究石窟寺的重要资料。史岩老师沿途骑马,历时数月到达敦煌,途中还发现了一些过去未曾被学界关注的石窟。
这些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学者和文博系统的专家一样,也非常重视考古学的第一手材料,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也是旁征博引,但他们毕竟和做现场考古的专家们不同,他们更关心的是时代风格的变化、造像形态的变化和艺术价值的高低。另外,许多从事艺术史研究的专家的学科背景也各有不同,有的是从美术创作转过去的;有的是学历史学、文学史的;有的是学哲学、艺术理论的……这也导致了他们并没有相对统一的方法论。例如有的专家比较习惯于倚仗历史文献资料;有的专家则有较多的个人的推测和想象,这些可能是艺术史专家和考古、文博专家之间会不同意见争论的原因。
第四是艺术家的研究方法。
艺术家对石窟寺和佛教造像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很早。根据四川美院龙德辉教授回忆,1954年四川美院雕塑系主任郭德乾教授就带着他们一帮学生在大足翻制石刻造像。目前这套翻制像在中国美院有一套早期的版本,现在保留完好。另外,中央美院袁运生老师也申请了一个国家课题,也是复制佛像,做了很多年,这是一个庞大课题。
许多从事艺术实践的艺术家,他们在研究石窟寺艺术和佛教造像的时候,在方法论上非常鲜明,也非常有特色。大致而言,艺术家的方法和石窟寺考古学恰好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对比。在今天,采用这种方法比较突出的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第六工作室,以张伟、杨靖为代表。
央美雕塑系六工的方法论与强调个人的眼光、经验和直觉判断。具体而言,通过反复在现场的观察、体味的基础,形成个人的经验,当面对一个具体对象时,他们不是学院派的引经据典,也不是拿着尺子丈量比对,而是凭眼光作出自己的判断。应该说这种方法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感悟式的方法高度一致,这种方法是感觉的,经验的,个人化的,拿他们的话说,就是培养“眼力劲”。
如何看待“眼力劲”呢?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看,人的眼睛是实践的产物。就是说,人的眼睛是历史形成的,经过了长期的审美实践,通过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临摹、体会,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直觉判断。看起来,这种自觉似乎没有经过逻辑论证和推理,也没有事实依据和理性思考,然而,它就是可以一眼中的,非常准确。这是因为,在人的审美直觉里包含了过去的思考、分析和积累,最后它以“眼光”的形式呈现,实际在背后,它凝聚了大量观察、临摹、比较、实践训练过程。
观察、临摹、翻制,直觉判断,是艺术家研究石窟寺艺术的基本方法。其中央美六工的方法论是一个标本。尽管他们也会考虑运用其它方法的可能,但如果始终坚持下去,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也非常好。
当然,不能说所有艺术家和雕塑家都采用他们的这种方法,但以张伟、杨靖为代表的方法非常典型,代表了相当多从事艺术实践的艺术家们的共性。在今天,重新认识这种偏中国传统的方法,可能成为对理性、科学研究方法的补充,构成一种互补关系,而这恰好是今天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所需要的。
三
为了进一步说明艺术家参与石窟寺艺术研究之后,在方法论上带来了哪些变化和进展,这里将以2023年7月25日至27日在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艺术研究院由学术院长赵立春策划,孙振华、冀少峰、鲁虹担任学术主持的“再造像——当代文化视阈中的石窟艺术”研讨会作为样本,从艺术家的发言中,来观察他们的研究方法。
为什么选用这个研讨会作为样本呢?
因为这次会议是文博系统研究人员、石窟寺考古学系统的研究人员、美术史领域石窟寺研究专家和研究石窟寺的艺术家之间的一次空前聚会,以上四方面的人员终于第一次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来讨论石窟寺艺术的问题,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师。在以往的石窟寺艺术研究中,石窟寺考古、文博系统、艺术史领域的专家一直是主要的研究力量,他们的研究方法论也相对稳定、成熟。近些年来,大量的艺术家介入到石窟寺艺术的研究,也发表了相当的研究成果,那么,艺术家们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为石窟寺研究带来了什么启示呢?这是我们所特意关注的。
在研讨会发言中,中央美院的雕塑系六工的杨靖没有正面谈自己的看法,而是介绍了三位同学在考察石窟寺之后所撰写的论文,通过这几篇论文,集中反映了六工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方法论特色。
蒲哲嘉同学的论文,在方法上表现出一种反学院、反架上的态度,他强调现场观看,通过艺术家用自己的眼光和古人产生神交,从而体会古代雕塑工匠的内心世界和他们所持有的观念。这种古今的神交也许不需要很多地查阅资料、而是强调现场的感受,用心去体会。
房颖同学的论文,认为粉本为中国古代雕塑创造者提供了样式参考,制约了创作者对空间位置的考虑。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房颖的论文是建立在假定基础上的,作者假设了一个确定的粉本。然而,从科学考古学的立场看,如果无法拿出具体的粉本材料,是无法进行后续推论的。房颖的价值在于,作为实践者,通过假定来讨论古代工匠的工作方式,讨论从粉本到立体空间的转化过程,实际上对还原古代工匠的创作情形,具体不可替代的意义。
陈家宏同学的论文,以北齐、隋代的造像纹饰作为研究对象,得出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纹饰始终都处在松紧繁简的轮回变化当中。这种“松紧松,简繁简”的演变历程,是优秀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从方法论上,也可以向陈家宏提问,即,这个结论的采样量有多少?从作者所看到的部分作品,能否推论出佛教像从北齐到隋代的纹饰都共同具备这一普遍特点?如果是的,那么不同地域的艺术家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取得这种风格一致性的?还有,北齐、隋代纹饰的“松紧松,简繁简”,是否可以作为优秀艺术作品普遍规律?一方面,陈家宏的论文需要回答以上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在他的论文中,发现了在方法论上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他认为,研究、创作的第一个步骤是:“把握作品整体气息”,这恰好体现了六工方法论的精髓,同时也是考古学、文博系统的专家可能会忽略的东西。
通过杨靖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中央美院雕塑系六工的方法论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延展空间。他们通过对学生眼睛的训练入手,培养学生对造像的感悟能力,以此为基础展开对佛像的研究,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一种人类学的本体论方法。它所引申出来的哲学问题是,我们是借助于某种工具来把握对象,还是通过人的眼睛直接把握对象?这是工具论和人本论的区别。为什么古代民间工艺会产生很多巧夺天工的东西?例如微雕艺人,他们对人的感觉的训练和开发达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可见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理性训练能够奏效的,而是人的感觉的解放和升华。很多时候,人的感觉是逻辑、机器所不能比拟的。
四川美院张强教授从视觉史的角度,指出响堂山石窟北洞高欢陵寝上“睡莲纹”的出现,是为了营造一种“天穹”之上的庄严。指示性的“侧面空间”与“上升空间”的莲花形式,成为北齐神武皇帝高欢的“魂魄家”视觉建设的重要方式。
清华美院孟媛博士设定了一个理想化的“假想观者”,在移动的视角中将北齐时期的水浴寺西窟内外的所有元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的视觉分析。目前视觉史和视觉文化的研究方法是艺术史研究领域的显学,这种这种方法的运用,为石窟寺研究带来了新的亮点。
天津美院的黄文智,采用了雕塑创作中的一种方法。雕塑创作着衣人物的时候,往往会先做出人物的裸体,把握人物的身体结构。他在研究佛造像的时候,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他有意把造像的外衣剥掉,还原成裸体,从而研究造像的身体结构。这种方法也许是一般做考古研究和文献研究的人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北京工大的李惠东在写作《佛陀的容颜》这本书的时候,采用了体质人类学的方法,更重要的,他是利用了雕塑家的造型优势,把握不同民族人像的造型差异。通过对人的比例、头骨、眼睛,鼻子,眉毛,嘴巴,胡须,发型等等部位造型特征的细致的比对和分析,阐述佛造像从“梵化”到“汉化”的演变过程。充分体现出了一个雕塑家的专业擅长。
中央美院王朝勇博士的研究也是另辟蹊径,作为艺术家,他在研究河北邺城地区造像的时候,着重从技法、材质与工艺的角度来进行探讨,作为一个有成就的木雕专家,他特别注意造像的刀法、镂空、插接等具体的技术问题,从技法与工艺的角度,看造像与当时的政治、外交、文化传承和思想观念的联系。
还有西安美院郭继峰,他从古代的画诀、塑诀来讨论、认识传统造像的规律。这是一种反推,根据从造像实践中所形成的模型、范式,来探讨造像的依据和观念,也是人们认识造像的一条有意思的途径。拿西方的造型观念来看,有些传统造像的比例是明显不准的。但是民间工匠有自己的说法。比如“身长腿短是贵人”,这个说法显然意识到了比例的问题。今天的审美,人们都欣赏大长腿,可是古人却认为身长腿短是贵人像,要那么长腿干什么?面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民间文化及其观念确实是影响到了我们过去的造像,这个角度对我们认识古代造像是有帮助的。
四
“再造像——当代文化视阈中的石窟艺术”研讨会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最激动人心的成果,是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时代高新科技融入到了石窟寺研究领域,它在方法论上产生的革命性的突破。从研究群体来看,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群体,即科技工作者出现在石窟寺艺术的研究中。这个群体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人们研究石窟寺的知识结构和方法论。
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中心陈洪萍的论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云冈石窟和大同市博物馆现存很多残缺的魏碑,它们字迹剥蚀,模糊不清。该中心一方面借助专业的几何和纹理采集技术,通过对题记进行了高保真三维重建,输出正射影像图,以三维打印、复制等方式对其进行处理;另一方面,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对碑刻文字进行识别。经过多组实验和训练,最终设计出一套智能算法,这套算法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最后能将无法辨识的模糊拓片图像变为高质量的清晰碑文图像。收到了显著成效。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突破了现有的研究模式。
西安交大贾涤非教授,承担了一个用数字化的技术对《文昭皇后礼佛图》进行造型还原的课题。贾教授的研究团队将历史文献整理、现场考察、3D扫描与建模、数字复原等多种手段融合在一起,对这件碎片化的珍贵文物进行了精确复原。
可以设想,如果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将来大规模地进入到石窟寺艺术和造像艺术的研究中,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说的尖锐一点,这种新的方法可能在相当部分取代传统考古学的那些耗时、艰苦的田野工作。我们设想,假如说有个学习能力超强的智能机器人来做考古的绘量工作又会怎样呢?它可能具备高度的视觉识别能力,可以发现也许人眼也许容易忽略的细微之处;如果拍照,它可以伸出任意的长臂的拍摄,取代过去搭架子的方式,而且还能避免透视的偏差……从石窟寺保存和开放角度的看,人们完全可以运用虚拟技术、增强现实的艺术,在数据的采集和扫描之后,可以无死角,无偏差地欣赏石窟艺术的各个部分,还原当年的石窟寺盛况……这些在技术上目前似乎是没有问题的。
高科技的引入,代表了石窟艺术研究未来在方法论上的趋势,即使它不能完全替代过去的研究方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解放研究人员的生产力,利用高科技做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这也许会带来石窟寺艺术和造像艺术研究的革命。
(来源:雕塑头条)
作者简介

孙振华,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雕塑学会秘书长,《中国雕塑》主编,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