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笑指龙门贺丰年180x194cm纸本水墨2025
那么,中国画的精髓究竟何在?郑天伦用“迹”与“象”二字概括。
所谓“迹”,是毛笔在宣纸上留下的生命痕迹。中国人独特的审美习惯,让笔墨线条本身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然而,当创作进入成熟阶段,笔墨必须超越描摹,服务于情感的承载。而“象”,则回归到造型的本源。中国画追求的从来不是逼真再现,而是客观物象与内心感受融合后产生的“第三形象”。这种经过主观提炼的形象,既熟悉又陌生,既具象又抽象,正是中国画艺术魅力的核心所在。

郑天伦 100×50cm 2025年
在艺术创作往往追求声量的时代,郑天伦的思考与实践,仿佛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反向叙事。他不急于打破什么,也不刻意证明什么,只是静静地在方寸水墨间,完成从技法到心性的修炼。
写尽乡关牵挂
西部大地的风,总带着沙粒与庄稼的气息,拂过郭峰的画纸已数十载。当他拿起画笔,墨汁在宣纸晕开的瞬间,那些扎根在西北大地的生命便苏醒了。“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就把文明的根扎下了。”石器时代的彩陶光晕、麦浪翻滚的金色海洋、夕阳下归牧的剪影,都让他沉醉。这片被外人视作“贫瘠”的土地,在他眼中藏着最蓬勃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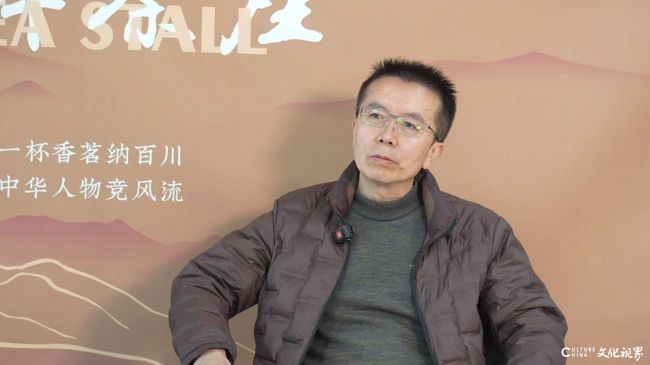
风里的故事听得多了,便读懂了人们对家乡土地的复杂情愫。那是祖祖辈辈“离不开、舍不得”的血脉羁绊,又混着年轻人面对外面世界“想挣脱”的迷茫与悸动。这份拧结在骨子里的情愫,成了他创作中最坚实的内核,催生出两个扎根现实的系列作品。一个将目光投向背井离乡的农民工,笔墨间藏着他们攥紧蛇皮袋时指节的发白,也印着他们在火车站台回望故土时,睫毛上沾着的晨霜与怅惘;另一个则是他的“家乡有待”系列,留守老人枯如老藤的手、留守儿童望向村口时的眼,都在他的笔下获得了沉甸甸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