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先生在”7、18谈话”15年后,一直没有放弃调查研究的努力,在为后人创造素材。“二十大开了,两个月拿出37万字的文章;春节8天写出《新质生产力与新国企》14万字,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弄得住院;李锦在沂蒙深山蛰伏的十年里,一年写政策建议与经济评论200多篇。这份以笔墨为犁、以岁月为田的深耕,正是完成调查研究“五经”的核心底气。
范敬宜与李锦的中华民族调查研究”五经”的对话,是一种”文不在兹“的悲伤情怀,是一种对中华民族新闻文明价值的绝对信仰,一种终生不渝的责任感与献身精神。
天下虽再无范敬宜,但范敬宜们的精神永存;
天下尚有李锦,更有无数传承其初心的后继者。
愿这份跨越十五载的对话,能够唤起当代新闻学子的觉醒。不负两位新闻大师的深情呼唤,不负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我辈目睹范李友谊,感知共谋新闻调查五经过程,其“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的悲怆,感天动地。他们一息尚存,仍思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动心弦。
愿中华民族新闻调查研究”五经”早日与世,让两位先生的理想之光,照亮新闻事业与教育事业的千秋之路。
(记者/徐子涵、吉海 来源:香港时报)
附:天下再无范敬宜(原文)

11月13日,是范敬宜逝世15周年的忌日,想起我们2005年7月19日最后一次见面。那是因为《农村八记》发表,讨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的事情。开始是温家宝写信给范敬宜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写信给范敬宜。范敬宜把我关于建立调查研究体系建议的信转给刘云山。这一天,我们讨论一上午。
那时候老范身体很好,神清气爽,谈兴也浓,老范希望我到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工作。在那一次谈话后,仅仅5年范敬宜就去世了。
我今年也到范敬宜那个年龄了。如果人生还剩下5年,老范与我商量的调查研究理论体系的事情,看来是很难实现了。我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悲哀。
1、范敬宜与清华学生的《乡村八记》
2005年7月19日,是个星期天,大雨滂沱。在北京万寿路一个茶馆喝茶,那时我还担任山东分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当时,老范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他把学生李强写的农村调查直接寄给温家宝总理。6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突出位置,刊登了温家宝总理的这封回信,并分8个部分选登了李强的农村调查报告,这件事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反响很大。使得他的思想与见解,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新闻教育界的天空。
我写了一封信给老范,认为这件事值得好好抓一下,在新闻教育界推一推,并就新闻教育的办学方向与课程提出我的看法。老范很重视,把我给他的信转给刘云山了。
温总理的信是这样写的:
敬宜同志,三月卅日的信及所附李强《乡村八记》早已收到,迟复为歉。《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你的几封信都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鼓励,深为感谢。专此奉复。敬颂教安。
这篇调查报告,出自一个心灵纯洁的学生之手,反映的农村情况是朴素、客观而真实的。但它肯定不会有官方机构做的调查系统、周密。是什么东西可能打动温总理呢?是这篇调查报告透露出来的这位同学的社会责任心和对农民的同情心。
于是,我在7月6日写信给老范,强调的是在新闻教育中建立社会主义调查研究体系问题。当然,我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处了。
我与《人民日报》、新华社认识的人很多,而当在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仍然讨论国家难题的,只有一个老范。我们都是农村改革新闻宣传的过来人,有一种心灵的默契。谈论的话题中心完全是国家的事情,决没有个人、家庭与单位的锁事。这是一个大文人与小文人的纯粹对话。国家难题、农民情绪、新闻发现学、调查研究的创新,这是连接我们关系的基石。差不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谈,这是我和所有的官员所没有过的一种默契与“深交”。我们的友谊,是一种和谐的平等,是无私的交流。
那天见面,就是老范、胡颖兄与我三人。老范是骑自行车来的,雨下得很猛。一个74岁的老人,骑着自行车,披着雨衣。我看了心里发热。
在茶社,我先点了个500元一壶的明前茶,老范说:“李锦,你个老土,北京的高价茶多是包装好,里面是一个样的,就是这个”,他点了壶50元的,胡颖劝说,就听老范的。我还是点了个200元的。
我们还是从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李强那一个调查说起的。老实说,对于当代新闻教育的象牙塔形象,我是不投赞成票的,言必称美欧现象,过于强调传播技巧技术,忽视对中国民情、国情的研究,这违反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本质,容易把路走歪,方向弄错,包括对清华大学的新闻教育,我也毫不留情的提出批评意见。清华大学应该培养”国”字号的记者,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包括中央电视台搞深度报道的记者,重点是记者,而不是编辑。这种记者应该有大气魄、大责任,很强的研究能力,是属于智囊型记者,对治国理政能提意见。首先是"知情",就是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即"三情"。还有“三心”,这便是良心、同情心、责任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办学,既脱离庙堂又脱离江湖。如果说江湖,那是西方新闻学的江湖,与中国的老百姓关系不大。老范去了,一下子把清华大学的新闻教育接了天线,接了地线。他不光说了,而且做了;不光自己做了,而且影响政府首脑也这么做。利用他的威望和社会关系,为国家新闻队伍建设、为新闻人才的培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重点是讲调查研究和新闻教育的事情。老范收到信给我打了电话,说自己脱离了一线,不了解基层,很可怕。说你有时间到北京来看看我。我连声答应,好的,好的。
我与范敬宜的语境是农村改革。我很佩服范敬宜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同时,他对党的新闻事业又十分执着,对新闻人才总是爱护和鼓励有加。他在《满江红·赠人》一词中写道:“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到峰巅仍自朝乾夕惕。当日闻鸡争起舞,今宵抚剑犹望月。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这种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与茹苦如饴的精神境界在他后来执教清华时,成了一种教育理念,就是加强实践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

《莫把开头当过头》是范敬宜1979年5月发表于《辽宁日报》的评论文章,后被《人民日报》转载。该文在改革开放初期引发广泛关注。
2、与范敬宜讨论调查研究“五经”
坐下来谈话,还是中国新闻教育问题。重点是老范听我谈,我滔滔不绝,他不断插话。
我和老范讲,你把中华民族的调查研究传统、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引入新闻教育中,为中国新闻教育界填补了一个空白,功莫大焉。
因为话题是《乡村八记》,我认为中国新闻界最有活力的是1978年至1984年农村改革这一段,可惜后来这一批人或则年老,或则当官,不能深入基层了。尤其是这一阶段的经验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提升,没有上升到规律层次确认下来。现在当旺的更多的是1982年后参加工作的,他们没有那一段经历,认识总不够深切,也不到位。再后来从国外回来的博士,一下子钻进方法论、技巧论里去了,对唯物论、反映论不够重视。我们不能培养美国式的新闻人,也不能坚持陈陋的东西。急需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与新闻发现学的理论体系,老范深表赞同,忧戚之心,溢于言表。
我和老范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史上,应该有一套调查研究课程。我说可以写5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史,加上中华民族调查研究史,黄帝内经、孔夫子的“每事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的漫游,都是调查研究的典范。再写一本《调查研究学概论》《新闻调查研究方法论》《调查研究发现学》《调查报告写作学》。先弄出5本书来,下面再一本一本地增加,把调查研究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
老范说你是调查研究“五经”呀。我们说起孔子的教育事业的开拓,始于六经。孔夫子53岁被人家赶下台,颠沛流离15年,68岁周游列国归来。老了,就安心教育,编了五六书。以《诗经》为文学课,以《春秋》为历史课,以《礼记》为道德课,以《尚书》为政治课,以《易经》为哲学课,还有体育音乐舞蹈方面编了一本书,叫《乐经》,后来失传了,就剩下“五经”。他与学生的对话,编了一本《论语》,相当一本论文集。最后6年时间,孔子留下中国的儒家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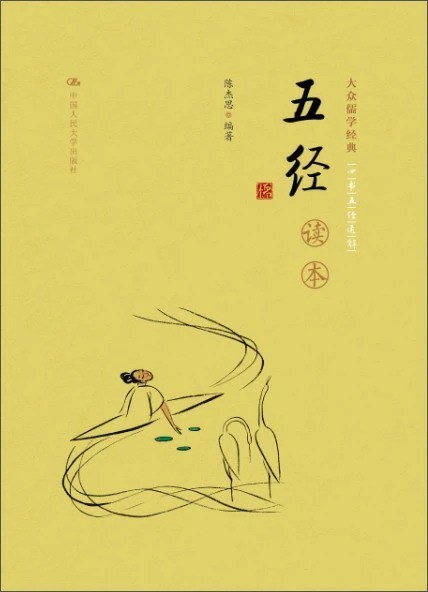
我们又说起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美国记者斯诺问毛主席,为什么从苏联、法国、日本、德国回来那么多人,最后是毛主席坐住了“一把手”交椅。毛主席就回答他,我和他们比无非就是会总结二字,就是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