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心的人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我们在茶馆里坐两个小时,外面雨噼噼啪啪地响着,而这屋内只有老范、胡颖兄与我,非常安静。
雨停了,老范架着自行车,披着雨衣回家去了。他坚持不再吃饭,说茶喝了,话说了,心也到了。他七十四岁高龄仍心系国家新闻教育的未来,关心未来的新闻人,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望着他在雨中独去的身影,想他“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的情怀,眼角有点发湿。
过了四年,老范走了,心中很是伤感,曾经关心和帮助自己的人一个接一个走了。而党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传统,也没有人有像穆青、范敬宜那样竭尽全力地讲了。后来的新闻领导人总是十分强调做好工具,而极少讲对人民负责任的话了。
其实“乡村八记”是老范办学是重视对国情的研究,培养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的记者,而不是技巧型的操作者。我一直认为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匠气过重了,多出自表现学一脉,发现学一脉太弱。共产党长期执政,更需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建言献策的人才。这是国家教育的大问题。
老范一心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的理论体系终未能成就。现在老范离开我们15年了,和老范那次见面也20年。这20年来,中国并没有出现调查研究的“五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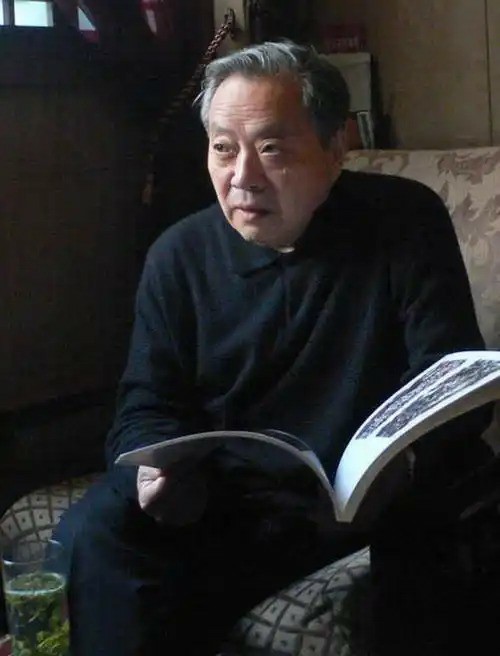
我现在和老范见面那一年,是同一年龄了。我这20年一天也没有懈怠。74岁了,还在基层调查研究。我知道,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每天不写一篇文章,我就觉得在虚度。一年写200篇经济评论与策论文章,都是关系国家难题的事情,天天像打仗似的。
可是想起老范74岁身体那么好,谈笑风生,还骑着自行车赶来与我喝茶,没有想到仅仅五年他就走了,我渐渐地有些不自信起来。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活5年,我们师徒当时商定的新闻调查研究“五经”,也一直没有落实。
后来我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江苏省委党校、中化集团等许多地方讲调查研究的课。休息的时候,一些研究生、博士生提出来:“李老师,您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我说,最大的遗憾是我的一身调查研究本事失传?
有学生说:“老师,你收我做关门弟子吧,我能吃苦。我想为国家做事。”
我说:“你们不能。”
学生问:“为什么?”
我说:“本事是练出来的,需要时代巨变高岸深谷的大条件,需要顶天立地的大胸襟,需要烈火金刚的大苦难,需要含辛茹苦的大勤奋。你们太安逸了。”
中央党校、山东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硕士们到九间棚参观。我领他们九间棚的题匾“望龙阁”,看柱子上写的“顶天立地胸纳乾坤气,高岸深谷笔吐惊雷声”,看进门门匾“蹲点”二字,看雕刻的《母子情深》,讲解《龙顶山书院记》里我的核心价值观“时代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进步引领力”。其实,我的全部秘密都在这里了,读懂的能有几个?

我曾经为我井喷式的写作而自我安慰。我住在山间百姓家,远离尘世干扰,不畏浮云遮眼,只缘心在最高层。我到这个年龄已经没有名利金钱地位的诱惑了。对于我来说,都没有什么挡着我的前行了。前天,青年时期的朋友史好泉到九间棚来看我,看我70岁仍一年发表39个整版的理论文章,他说你这一辈子值了。我欲言又止,其实,我是不值的。我应该做的,不是这个。
我曾经为我受的冤枉而不能自安,不白之冤,何时洗清。可我知道,苏东坡,如与那些朝中宦官斗争,说不定早就死亡。自己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了。国家事大,个人事小,我只求为国家做事,个人得失早已置之度外。我的事情,只由历史回答了。
我生活并不幸福。因为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弥补不了。如果有哪个大学聘请我去当专职教授,有个创造的、实验的情景平台,我就把调查研究的“五经”写出来,为我们国家填补这一空白,完成老师范敬宜的期待。
这20年,我天天打仗,可是我似乎不该在这个战场。然而,竟越陷越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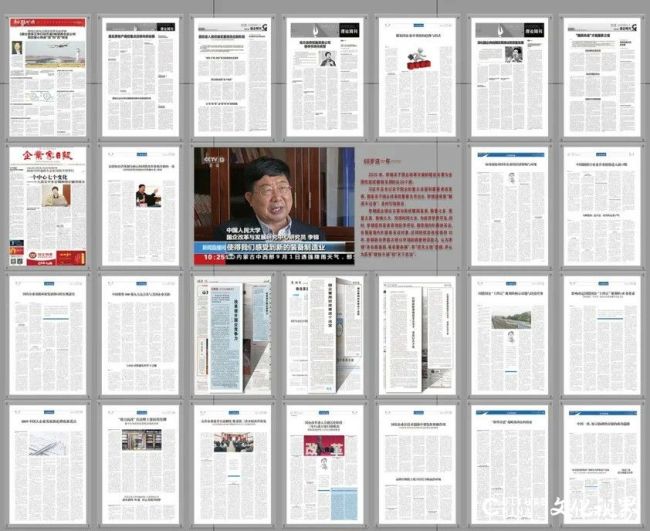
展览一页说明:2020年,李锦68岁这一年,他写的关于国企改革方面的理论文章为全国性报纸整版采用的达39个版。李锦的国企理论文章,以重大主题、最快速度、贴近实际、解决问题为特色,常常在晚间新闻联播后当夜写出,发挥“第一时间”引领舆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