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那么,这些人物只能对应于抽象意义上的“所指”,当人们说到“篆刻”一词的时候,便会联想到米芾、赵子昂、王冕这些非“篆刻”本身的具体人物存在,尚不足以证明他们篆刻的语言形式符号有充足的物理存在,以及篆法、刀法、布形规则、视觉形象乃至流派性等因素。比较起来,若将他们纳入篆刻史来考量,谓之启文人篆刻非“能指”的“先河”较为妥当。


事实上,北宋士大夫阶层注重的金石鉴藏,其核心旨趣在于补证经史,金石笔法概念尚未形成,因此无法对“帖学”“帖系篆刻”乃至绘画的写意用笔产生本质影响。帖学以用笔的细腻书写为核心,追求飘逸、潇洒、妍媚的风格,强调点画的使转和笔锋的灵活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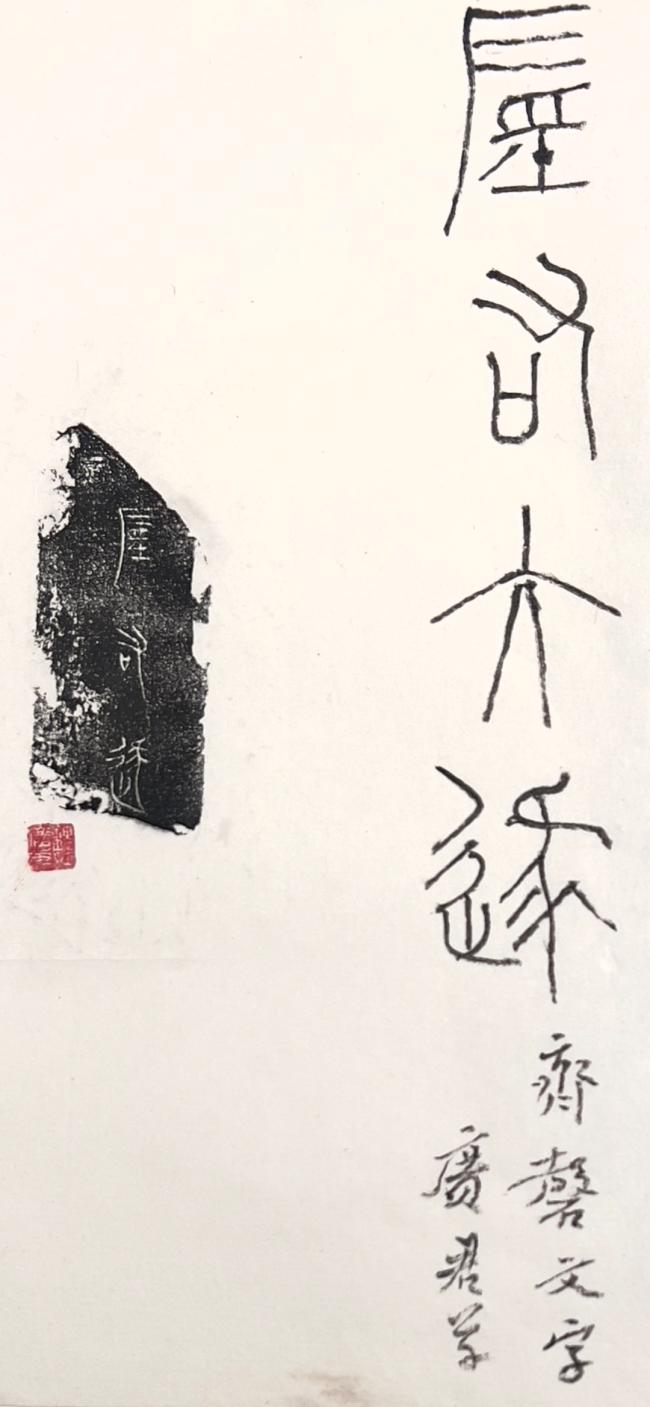
针对南北朝而言的“透过刀锋看笔锋”,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帖学”创作观,透过刀刻的痕迹与质感,去演绎笔法的表现技巧和形式,及其可感知的符合帖学观念的书法风格。明白的人都知道,帖学从入手开始就有具体学习与发展的理路设置,可以大概的预见其风格样式的结果呈现。在审美上基本约束在二王体系之内,注重对唐、宋、元人墨迹自然流畅的行笔,气韵生动的追慕。这种情况到了明中晚期以后,对技法的表现力凸显目的性的要求,风格样式有了许多近乎程式化的设计表现。